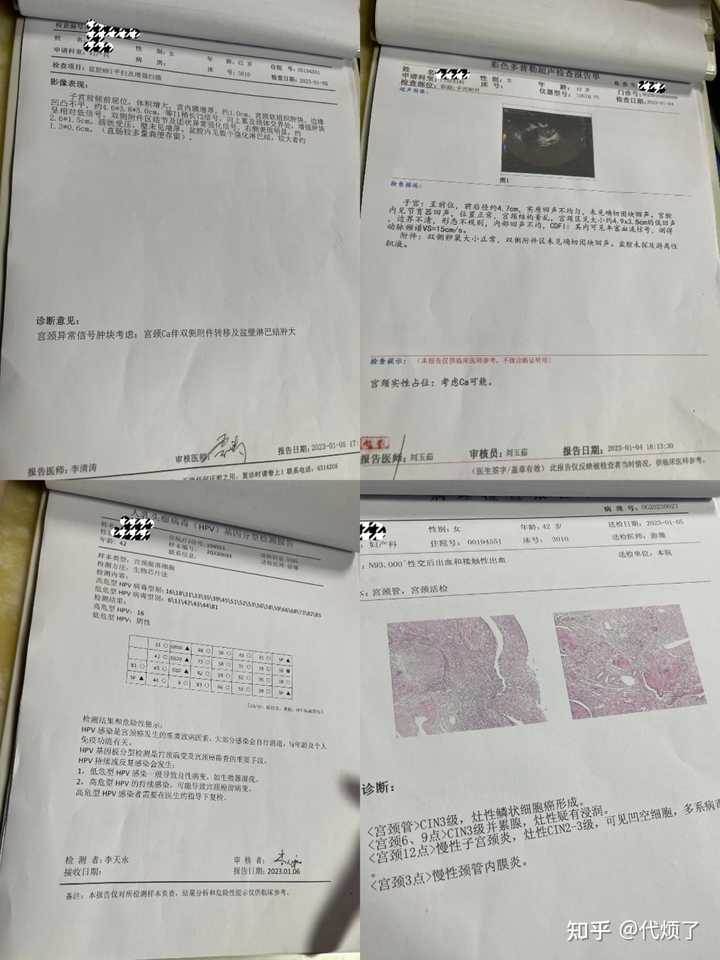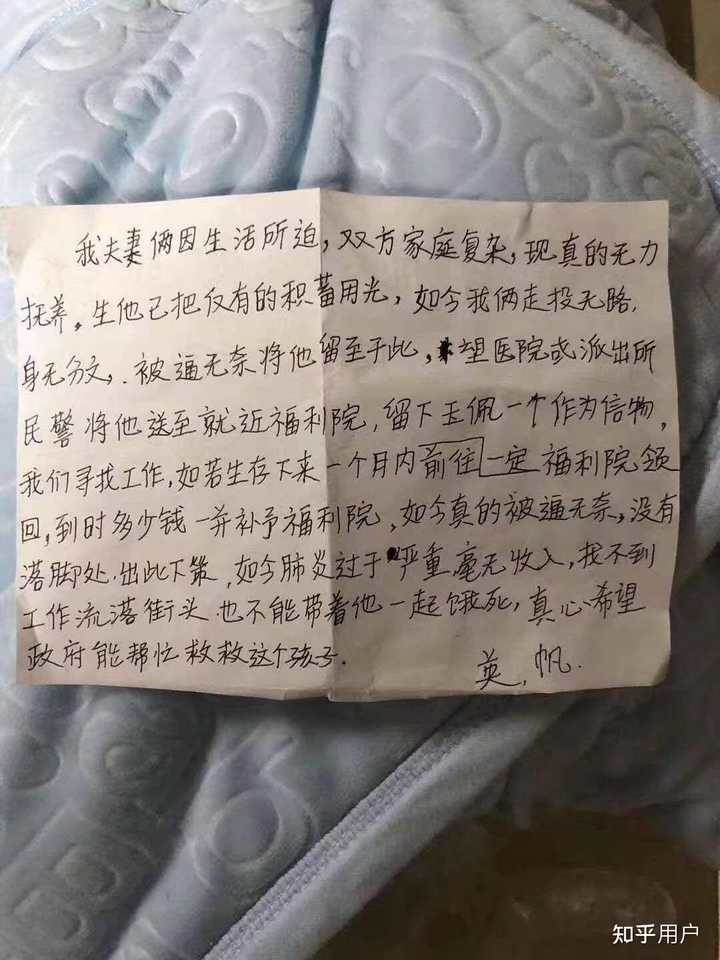最殘忍的是你本來有機會上手術台,活下去,或許康復下來,你至少有活下去搏命的機會。
你是清醒的,抓著女兒的手,流著淚,想活下去。
你的存款還有不少,每個月有退休金,你身體健康,你只是,不小心意外摔倒了,腦溢血。
你聽到三甲醫院的神經外科醫生在詳細和女兒女婿們溝通,在講解你的病情檢查結果,反復說這種情況可以做手術,建議做手術,要做手術盡快決定。
可是,他們說,要再考慮考慮,最后推出一個女婿做代表,要求醫生給一個明確的保證,保證做了開顱手術以后,人肯定能好轉。年輕的醫生說不能絕對保證。
于是,女婿女兒們說,連醫生都不能保證做手術以后好起來,那就是醫院為了搞錢,他們代表你選擇了保守治療。
你在icu陷入昏迷,情況惡化。
女兒女婿們又共同決定,把你從三甲醫院的icu轉院到中醫院的普通外科,你并沒有聽到icu醫生的警告,醫生警告說「這個情況轉院,腦出血的病人移動碰撞了情況很難再好轉」。
轉院當天下午,你回光返照清醒了短暫的時間,眼淚從眼角淌出,你嘴唇蠕動想說話,已經發不出聲音。
你最終,在這個中醫院的icu里去世。
你的骨灰安葬儀式上,有高價請來的陰陽先生按套餐內容念念有詞。
你留下的遺產和撫恤金由女兒女婿們分割,絲滑地匯入小家庭的賬戶。
這是你離世前十幾天的經歷,這本不應該是你生命最后的遭遇。
以上,是2019年家族里一個為人很好的老人,她的真實遭遇。在她回光返照,被送入中醫院icu搶救前,也就是從三甲醫院的icu轉到中醫院外科普通病房的當天下午,我和家人接到她家通知,說人可能不行了。
我們一家人趕過去,都知道是見她最后一面。她看到我們,人當時是清醒的,口不能言,蠕動著嘴唇比著口型,像是在喊我們的名字,打最后的招呼。眼淚順著老人的眼角往下淌,見到后十幾分鐘,就陷入半睜半閉的昏迷或者彌留。
我彎腰在她床邊,右手握著她的右手,握了一個多小時。她的手沒有一點回握的力氣,頭髮在icu躺的十幾天里沒有清潔過,油油的,一縷一縷散落在枕頭上,襯衣半開著,整個人毫無生氣地攤開。
在十幾天前,每一次見到都衣著整潔的老人,怎麼變成這樣了?
白色的床單,慢慢開始有其他家族的人過來,圍在病床邊。
這個大病房有三張病床,她在中間的一張。和其他兩張床的隔離,是兩幅從天花板垂到床腳的藍色床簾。
我始終握著她的手,明白這就是最后一面了。
一個五十來歲的矮小女護工過來,掀開斜搭在老人身上的被褥,熟練地褪下她的長褲,用紙巾給她清理下半身的衛生。
老人的女兒之一過來了,女護工邊幫老人擦拭,邊說著要家屬準備一些棉質的舊衣物,方便做尿片,給老人更換。又圍過來幾個家族的女性,都是長輩,關切地看著女護工的動作。
我間或搭話,似乎分裂成了兩個人。一個人在頭腦清醒地認真詢問護工,問尿片用什麼材質,大小,準備多少。另一個人抽離出來,知道這是無用的。因為老人的女兒之二正在病床的另一邊,悄悄和其他親屬說著「人可能不得行了」、「就是這兩天了」、「沒啥必要了」諸如此類的話。
我的聽力很好,隔著這麼遠,在嘈雜的聲音里還聽清楚了。
醫生過來了,女兒之一在詢問要不要給老人吃藥。
醫生說可以,吃一片xx,弄碎喂進去,再吃另一片xx也可以。
人群涌涌,我在病床的左側,仍然握著老人的右手,不知道在試圖傳遞點什麼,我好像是在人潮中給孤單的她送行,好像想把一點活人的溫暖通過握手傳遞給她,我好像知道自己在對她說:不要怕呀,我送你。
水來了,我松開老人的手。看人給昏迷狀態的老人喂藥,喂進去一點,灑了大半,胸口的衣服都打濕了。
再然后,我看到的是老人的墓碑。老人在生前就買了墓,真的,位置挺好的,只是這兩年掃墓,我們都沒有找到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