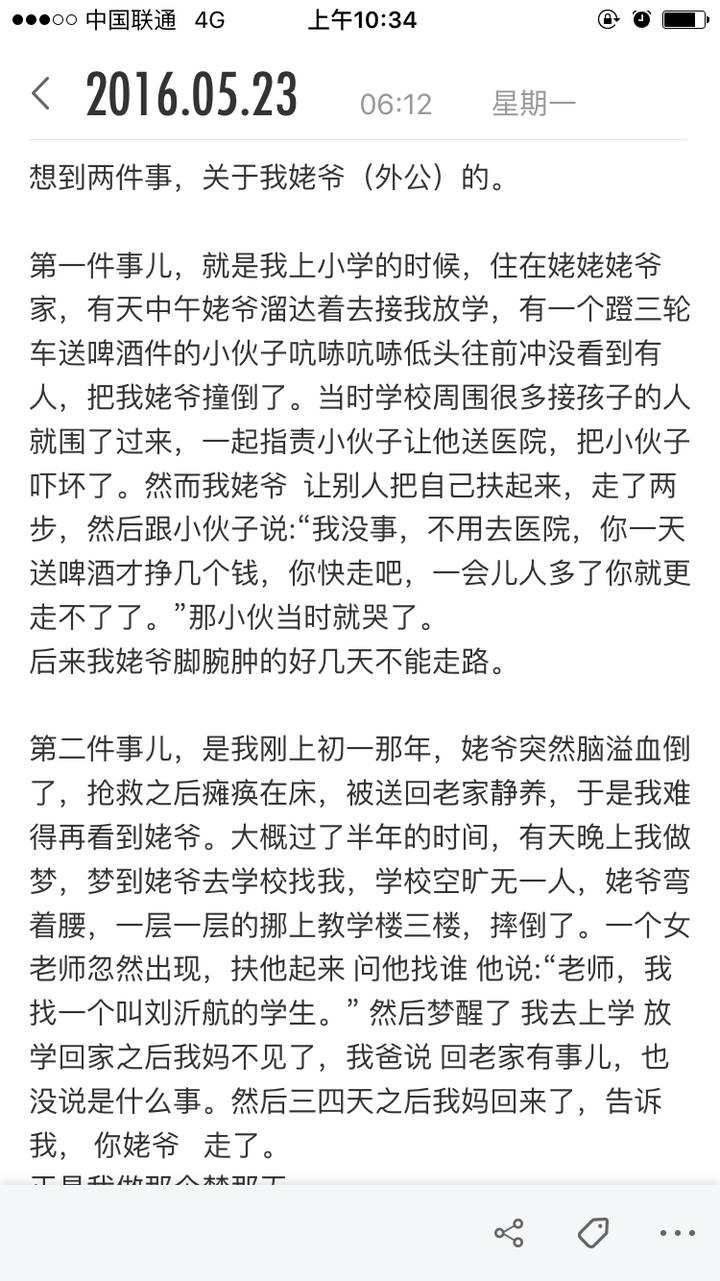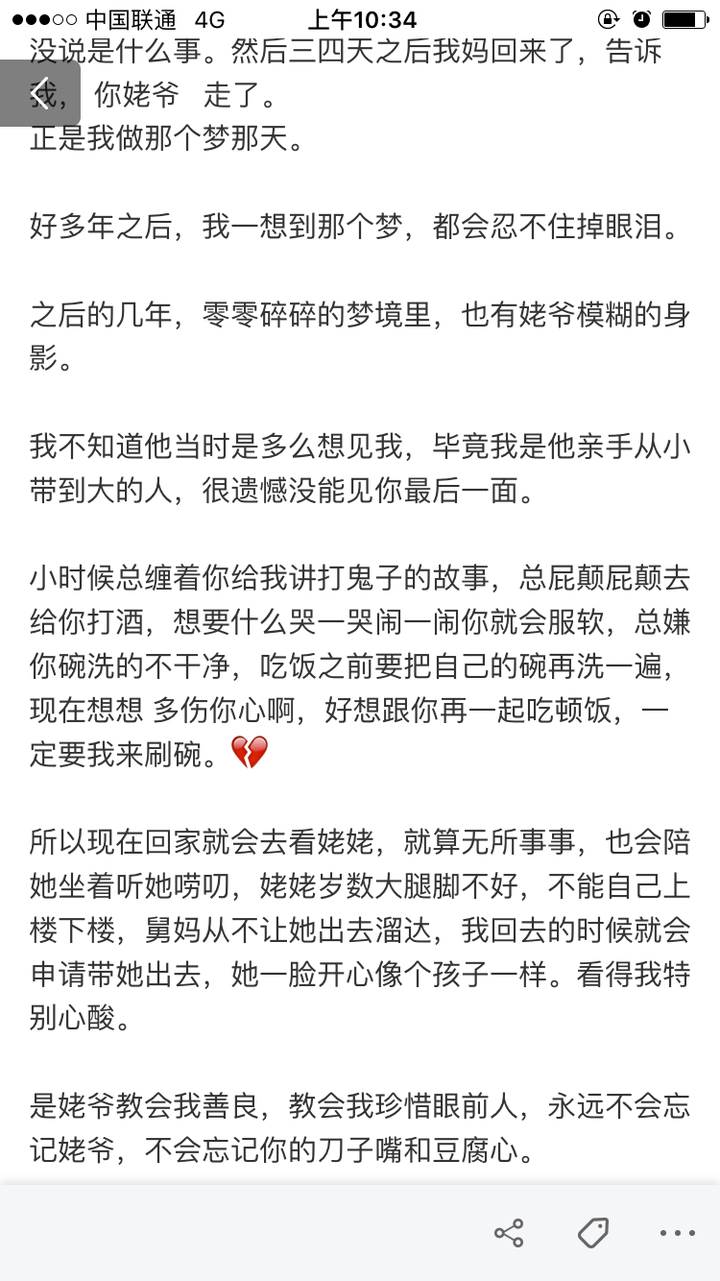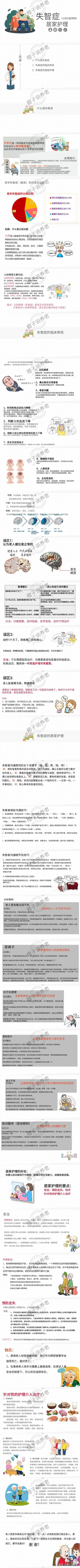我母親離世前幾天,一直心心念念要去看海。
我答應帶她去,但忙起來就忘了。
那天中午,她突然打電話給我,用很委屈的語氣說:「你來接一下我可以嗎?我找不到路了,輪椅沒電了。」
我說:「你現在在哪里?」
她說:「我不知道。」
我說:「周圍有沒有醒目的建筑,大房子什麼的?」
她說:「沒有。」
我說:「怎麼會沒有呢?酒店,加油站,什麼店子都可以,你隨便找一個我就能導航過來。」
她說:「沒有,我不知道。」
我說:「那你隨便形容一下你周圍是什麼樣子。」
她說:「我在一座橋上。」
我打開地圖看了下,旁邊的確有座大橋,我連忙跑過去找她。
兩百米長的大橋,我從橋頭跑到橋尾,沒找到她,趕緊又給她打電話。
我說:「你不要亂走,回到橋這里來。」
她說:「我就在橋這里啊,你到了嗎?」
我說:「我也在大橋這里,我找不到你。」
她說:「那你估計跑對面去了,等我過來找你。」
我說:「你就在原地等著就行了!」
打完電話,我一邊往橋對面跑,一邊仔細打量兩邊,從頭跑到尾,還是沒找到她。
她一個病到路都走不穩的人,坐著輪椅把自己弄丟了。
我徹底煩躁了,我給她發微信視頻。
我想看看她在什麼地方,可她手機拿的很近,我只能看到她的臉。
她一臉憔悴,臉色灰沉,嘴唇是紫青色的,額頭上全是汗水。
我說:「你把手機拿遠一點,照一下你后面讓我看看。」
她就盯著手機,也不說話,不知道在擺弄什麼。
我說:「你只要把手機拿遠一點,讓我看看你后面有什麼就行。」
她說:「等一下,等一下。」
我等了幾秒鐘,她還是盯著手機不知道在搞什麼。
我說:「你把手機拿遠一點!」
她說:「我不會!」
我說:「怎麼可能不會呢!你只要把手機拿遠一點啊!動一下手,把手機往前放一點!」
她哭喪著臉,好像這很難理解,還是焦急地盯著手機,不知道在擺弄什麼。
我說:「我求求你了,你讓我看看你在哪里,你這樣我找不到你。」
她說:「我知道了。」
然后還是沒有把手機拿遠。
我又催促了兩次,她莫名其妙居然把視頻掛斷了!
我徹底崩潰了,我罵了幾句粗口,罵我自己,然后給她打電話。
電話打不通,我又急又氣,頭都暈了,打不通,我繼續打,一直打,瘋狂打,打了一百多個。
終于通了。
我說:「好了,什麼都別說了,路邊有人沒有,你找個人問一下你在哪里。」
她說:「他們不理我……」
她話說了一半就不說了,我也明白了,坐著輪椅的她一看就是病入膏肓的人,沒人愿意擔風險做好人。
我要瘋了。
我想不通,曾經那麼果敢精干的一個女人,如今怎麼會變成這樣。
連將手機拿遠這種事都沒辦法辦到,我那時恨不得從橋上跳下去。
後來,她遇到一個小伙子,小伙子把準確的地址告訴了我,我終于找到了她。
她在一公里外的另一座橋上。
她坐在輪椅上,以為我要罵她,她低著頭不敢看我,強裝鎮定。
小伙子說:「太危險了,她一直在逆行,輪椅都跑到馬路中央去了。」
我謝過小伙子,勉強冷靜了下來。
小伙子走后,我說:「你現在是怎麼回事,連手機拿遠一點都不會了嗎?」
她不說話。
我說:「你回答我啊,這是為什麼啊?你到底有什麼想不通的。」
她不說話。
我拿出手機,模擬了視頻的樣子。
我說:「你看,這是視頻的時候,我叫你拿遠一點,你只要用手往前一點就行,你不會嗎?」
她還是不說話。
我沒轍了,慢慢推著她回家。
那天太陽很大,下午悶熱的不行,可我寒冷徹骨,滿心絕望。
……
……
……
天將要黑,我和她才堪堪回到家,從中午折騰到晚上,兩個人都累的夠嗆。
我隨便炒了兩個小菜,又從外面買了幾盒米飯,叫她吃飯。
她嘗了兩口,說:「真好吃,今天餓了,我要多吃點!」
我說:「你吃吧,沒人跟你搶。」
母親的廚藝其實很好。
雖然我在酒店掌廚多年,自認廚藝是及不上她的,她也從沒這麼夸獎過我。
其中一道菜是雞翅,一共有五個,我和她各吃了兩個,碗里還剩一個。
我說:「我吃飽了,還有一個雞翅你吃吧。」
她點點頭,一聲不吭地夾進了碗里。
若是以前,這種情況她一定不會自己吃,就算留過夜,也一定要留著給我。
她的病越來越重,食量也越來越少,在我印象中,這是她唯一一次,吃了足足兩碗飯。
我原本對她有怨氣。
她病的那樣重,卻只身一人跑到這麼遠的城市來。
雖然這是我曾經給她的建議。
她的病,是風濕性心臟病,因為老家多山多雨,每到冷天下雨,她的腿就會開始滲水,她的肚子也有積液,還伴隨著頸部血管的猛跳。
她總是睡不好。
在她病的沒那麼嚴重的時候,我告訴她,南方有一座小島,四季如夏。那里空氣非常好,并且距離大海很近,她去住一段時間或許會好一些。
她反對我,說那麼遠,光是路費都得多少錢?她心疼錢。
直到兩年后,她的病情越來越重,不光身體越來越差,精神也越來越恍惚,乃至幾次入院,醫生都下了病危通知書。
她有一天打電話給我,說她要去海市。
我說:「你病成這樣,就別胡思亂想了,老老實實在家養病吧。」
她說:「老家太冷太潮濕,身體受不了了。
」
我說:「你去那麼遠,誰來照顧你?」
她說:「我自己能照顧自己,我的病已經好多了!」
一個病人說的話,我本不該相信,但我確實信了,電話里她很精神,我以為她真的好了一些。
我說:「好吧,到那邊有什麼事你給我打電話。」
沒過一個月,我接到了她的電話。
準確的說,是她的護士打電話給我,說她摔倒了,傷到了頭,正在住院。
我得知這個消息,整顆心都吊了起來。
她在電話里委屈地說:「我摔倒了,我也不知道為什麼,這次摔的這麼厲害。」
我說:「你為什麼不小心一點?」
「你明知道你身邊沒有人,為什麼不小心一點?」
她說:「你過來好不好,你爸爸逼著我回去,我不想回去,這里環境很好,對我的病有好處。」
「只要你過來了,他們就不會逼著我回去了。
」
我糾結又煩躁。
我有穩定的工作,如果去她身邊,一切都得從頭再來,雖然可以靠自由職業賺錢,那一定也比不上這份工作。
可是,一想到她孤獨一人回去老家,那麼寒冷,那麼多雨的山城,我的心就軟了。
我說:「我這兩天辭職,盡快過來。」
她高興的像個孩子,在電話里說:「那太好了,那太好了。」
當我見到她時,她坐在輪椅上,已經病的不成人樣。
她的臉,她的手,浮腫而紫青的皮膚緊貼著骨骼,渾身看不到一絲好肉,她病到了這個地步。
她說她的摔倒,是因為輪椅的兩個踏板是分開的,她下輪椅時,腳不小心踩進了踏板間的空隙,于是被套倒。
我強忍心痛,嚴厲地告誡她,下輪椅時一定要找一個能抓扶的地方,先抓扶,穩住身體,再下輪椅,我不可能整天盯著她,我必須工作。
她默不作聲。
她后面沒給我添過麻煩,直到這次走丟。
我原本對她有怨氣,怨她騙了我,讓我答應病的這樣重的她,走的這樣遠。
對自己更有怨氣,她是一個病人,粗心大意可以歸結為身體機能下降。我作為一個正常人,來到她的身邊,還是沒能照料好她,害她擔驚受怕了一個下午。
我想,既然她愿意吃我做的飯,接下來我就認真給她做幾天飯好了。
我告訴她,我會盡快找個時間,帶她去海邊轉轉,前提是她老老實實在家待幾天,不要一個人出去亂走。
吃過飯,她有了精神,她解釋說:「今天輪椅電沒充夠,所以才叫的你。」
我說:「就算輪椅有電,你病的這麼重,也不能一個人走太遠。」
她假裝不高興:「什麼病,說不定我能活到八十歲呢?」
我說:「又沒人不讓你活。
」
她就笑。
此前的萬種怨愁,經過這次晚餐,消散了大半。
可我怎麼也想不到,這竟是我和她的最后一頓晚餐。
……
……
……
……
她年輕時愛吃辣,重咸口,很少吃肥肉。
她那時卻吃不得辣了,鹽也不敢多吃,開始愛吃肥肉,她瘦的皮包骨,坐著都被硌疼,認多吃肥肉有利于長肉。
隔天中午,我還在考慮,晚上要給她準備怎樣的飯菜。
突然又接到她的電話。
電話那頭是個女聲,說她出事了,現在在醫院,讓我趕緊過去。
我坐在出租車上,氣的牙癢,心想她一定又一個人出去了,昨天才剛剛走丟,今天又進醫院了。
為什麼總不叫我省心。
明明那麼叮囑她了。
我在車上想了很多,想發火,想接著該怎麼辦,是帶著她回老家,還是辭去工作,晝夜看護她。
不論哪一種選擇,都非常麻煩,我想不管怎麼樣,得對她下最后通牒了。
我去到醫院,找到她,她躺在病床上,一直唉唉地喊著。
我說:「怎麼回事?」
她聽到我的聲音,努力地想要抬頭,可病床是平的,怎麼也抬不起來。
我趕緊走過去,發現她眼睛大大地睜著,一直在流淚。
她的頭上纏了些繃帶,半張臉都是干掉的血,我摸了摸她的額頭,皮膚緊緊地繃著,燙的嚇人。
她看到我,像是想要說話,可支支吾吾,什麼也說不出來,還是不斷唉著,像是疼的。
她是很要強的一個女人。
從小到大,我從沒見她這樣過。
她得是傷的多重多疼,才會喊出聲來。
我大腦一片空白,路上的所有想法和怒火都化為了烏有。
護士告訴我,她是被人送到醫院來的,已經半個多小時了,剛剛做完檢查。
我問她:「是誰送你來的,你是怎麼受的傷?」
她看著我,「是……是……」齜牙咧嘴一會兒,什麼都沒說出來。
我說:「你別急,慢慢說,你是怎麼受的傷?」
她痛苦地擠眉咧嘴,好一會兒才憋出幾個完整的字眼:「不知道。」
我想她一定是傷到了某些神經組織,沒辦法正常說話和思考了。
我只好問她:「是不是輪椅,你是不是又被輪椅套倒了?」
她的頭,費力地左晃右晃,像是在回憶,過了一會兒,終于點了點頭,說:「嗯!」
我說:「為什麼啊,我叫你不要一個人出去,叫你下輪椅得先找個抓扶的地方。」
她斷斷續續地說: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,我去買菜,莫名其妙就摔倒了,今年運氣不好。」
她的外套浸透了血,我摸了一把,沾了一手。
我一陣陣揪心。
我說:「怎麼會莫名其妙呢,還運氣不運氣,你就是不聽勸!」
她不再說話了,像做錯了事,連呼痛的聲音都小了些,這令我更是痛心。
醫生把我叫去談話,說她需要住院觀察,因為發現腦中有輕微出血。
我想她傷這麼重,住院最起碼也得十天半個月。我繳了費,索性打電話把工作直接辭了,做好了持久戰的準備。
礦泉水,卷紙,護理墊,尿不濕,馬扎,我百度了一下醫院陪護需要的物品,買了一大堆。
回去病房,她又盯著我支支吾吾地說話。
我問她怎麼了。
她憋了半天,說她忘了。
我很懷疑她不是因為輪椅受的傷,而是被人撞倒的。
因為有一次她被撞傷了小腿,也沒有告訴我,直到傷口感染被我發現,在我的逼問下才說出口。
我說:「怎麼能忘了呢,你再仔細想一想。」
她怎麼也想不起來。
她痛苦而氣惱地說:「怪了,怪了,我明明記得的啊!」
我注意到她嘴巴很干,問她:「你是不是想喝水?」
她愣了一會兒,重重點頭:「嗯!」
連喝水這種事都說不清楚,都能忘了。
我賭氣地說:「等你出院,我帶你回老家。」
她閉著眼睛,臉上痛苦帶著些委屈。
我狠心地想,不管她愿不愿意,一定得帶她回去了,一邊打開礦泉水,倒在瓶蓋里喂給她。
她哆哆嗦嗦地喝,可沒喝多少,就翻了白眼。
她四肢古怪地扭曲著,渾身劇烈的顫抖。
她被一路推進重癥監護室。
我沒想到她會突然這樣,整個人都蒙了。
家屬不能陪同,我只能在樓道里或坐或立。
每隔幾個小時,醫生就打電話叫我一次,討論她的病史等情況。
我熬了一天一夜,恍恍惚惚,坐在樓道里睡著了。
我做了一個夢。
夢到我躺在床上,她忽然推門進來,還是那副瘦的皮包骨頭,病入膏肓的樣子。
她頭上纏著紗布,手里提著一袋子菜。
我問她:「你不是在住院嗎,怎麼回來了?」
她說:「我已經好了,住院要不少錢呢。」
我說:「就知道錢,你以后絕對不能一個人出去,買菜也不行,我可以去買。」
她提了提手里的菜:「我知道了,今天我給你做菜吃。」
我說:「買的什麼菜啊?我可不吃肥肉。」
她得意地笑著:「都是瘦肉,便宜的很!」
我是被醫生的電話吵醒的。
醫生告訴我,所有的搶救藥都用完了,病人已經不行了,要我趕緊進去。
我一邊換隔離衣,一邊麻木地簽了很多文件。
走到她身邊時,她一臉憔悴,眼睛緊緊地閉著,她快要走了,卻無法醒過來跟我道別。
我平靜地站在那里,看著她,不知過了多久,直到護工告訴我,她走了。
我腦子里嗡的一聲,一片黑暗從頭頂壓下來,像是有什麼東西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