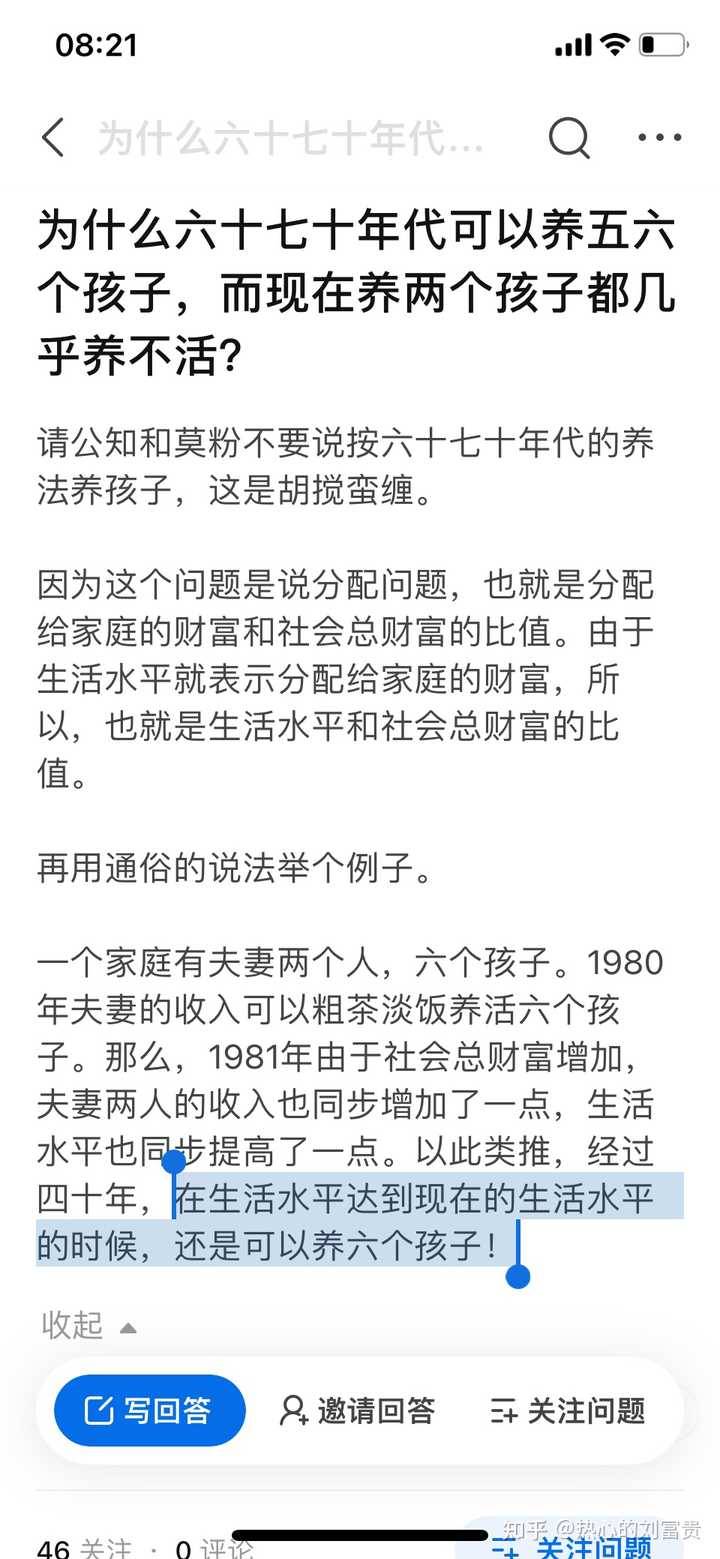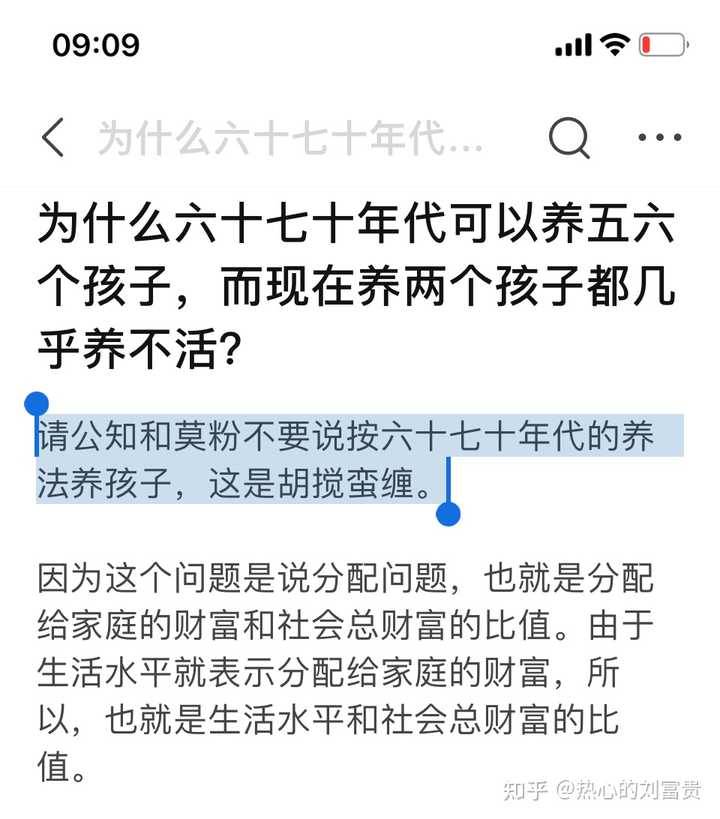你以為是養了五六個孩子,實際是生了十個,活到成年的就五六個。
我爸是個故事大王,我也特愛聽他講以前的事兒,以前他們的童年生活,我還真略知一二。
自打記事開始,我記得我爸爸排行第二,奶奶一共四個孩子。
後來我才知道,我奶奶生了八個孩子,我爸爸壓根不是排行老二。
在我大伯之后,我奶奶生了雙胞胎閨女,閨女沒活下來就夭折了。當時就是很粗放,家里炕上生下來,孩子臉青紫,拍了沒什麼呼吸,就直接埋了。
接著生了一個閨女,就是我大姑,大姑倒是活到成年了,只是在我小學的時候出車禍去世了。
我大姑之后又一個男孩,真正排行老二。他死于甘肅大饑荒的時候。
那時候,我爺爺胃癌,切了胃,去省城療養了,帶著我奶奶一起。
沒錯,就是這麼隨便。
三個孩子丟家里,給點糧票,讓他們自己弄吃的。
比饑荒來得更早的是甘肅南邊的流民,剛開始是討飯,後來就是搶了。
我姑姑和爸爸聽爸媽話,餓得翻白眼,但把家門頂住,死活不出門。
我爸爸的那個二哥,當時十幾歲,正是青春期呢。他性格又跳脫,男孩子發育期餓得守不住,就快啃姐姐和弟弟了。
他就出去了,說是找樹皮野菜吃。之后就再也沒回來。
過了幾天,紅山窯的親戚騎自行車來了,說是接到了爺爺奶奶的信,給家里帶了口糧。
就那長毛了的黑面饅頭,一團團青色的,一手提袋子。
我爸和姑姑如獲至寶,用火烤了,然后就靠著這個活下來了。
紅山窯來的族叔問起老二,說是出去,就意識到不好了。
他主動去幫忙打聽,縣城了找了一圈,最后在后山墳崗找到的。
通過衣服鞋子確定了人,已經是橫尸野外了。
有知情的人說,他們一群青年,在這里餓極了,挖死人骨頭吃,吃完了肚子大得像是懷孕十個月,趴在河邊吐,吐到後來就吐膽汁,後來就是血水。
老二就這麼沒了。
什麼時候記起老二來了?
我媽媽和我爸新婚。清晨起來,隔著玻璃看到花池邊有個人,以為是我爸爸,就喊他名字。
喊了幾聲,人轉過來了,我媽媽昏過去了,高熱不退,滿嘴都說院子里有個人,藍褲子綠衣服的青年,嚇人得很。
我奶奶這才想起來,老二走得時候穿得是這身。小崽子恨我爸爸占了他老二的位置,來霸占媳婦了。
找人做法事,燒了寫老二名字的紙條,這才消停了。
我爸爸之后,又生了一個男孩。但這個孩子怎麼沒的,我奶奶都忘了。
問我爸爸,他們隱約記得是會走路的時候,走失了,就沒找回來。
那時候被人拍花子給拐走也很正常。
之后生了我小叔,小叔是最后一個孩子。
我奶奶這時候已經過了生育年齡,就沒再懷孕過。
我爸爸回憶起他同齡的孩子,也是還沒成年就死了個把了。
我們巷子口有一口姓魏的,家里九個兒子,還沒分家,主要靠打鐵生意。
他們家的魏九和我爸爸是同學,魏老大的兒子也和我爸爸一個班級。
我爸爸說當時是看著魏九死的。
他們十幾個男孩去后海子的池塘里游泳,游完了上岸,脫了褲子在草坪上曬身子。
魏九人稱魏猴子,爬樹一絕。他看電線桿上有一窩鳥,就準備上去掏鳥窩。
大家曬得舒服,沒人搭理他。
他就硬抓著自己的侄子魏二尕,讓他當梯子,踩著二尕的肩膀往電線桿上爬。
魏二尕也不樂意當梯子,奈何魏九是自己小叔叔,怕他回去給自己爹告狀又要挨打,就勉強讓他踩了肩膀一下。
等魏九上去,他立馬翻著白眼,罵罵咧咧去河里洗澡了。
等爬上去,還是夠不到鳥窩。
魏九就單手撐住自己,猛往上一頂,手摸到鳥巢了,但濕漉漉的頭頂頂到了電線上,整個人僵直了,頭頂冒火,劈哩叭啦就摔下來了。
等魏二尕把自己爸爸喊來,魏九死透了。
魏老太在自己小兒子的白事上面色如常,吃了幾大碗丸子清粉湯。
反正她生了九個兒子,孫子都有一堆了,也不缺這一個小的。
我爸爸還有一王姓同學。
他們結隊去偷農場的豆角。回來的路上,王突然想起要去北海子劃船。
本來就暑熱,還被農場老頭追了幾百米,我爸他們沒人去,都想著回山后的破廟里燒蠶豆吃。
他們一起的錢大個子想趕緊走,就嚇唬王,說北海子那池塘里有索命的水鬼,誰黃昏去劃船,就要誰的命。
王被一激,大罵錢是膽小鬼,個子大,卵蛋小。他把裝在褲子里的豆角掏出來給其他人,轉頭就自己去劃船了。
過了幾天,我爸他們見王家辦喪事,才知道王給劃船淹死了。
那時候,這種事情也沒人找警察啥的。人撈上來,就給埋了,也沒人找我爸爸問過情況。
當年根本沒什麼限制和教育措施。小孩游泳、劃船、觸電死亡,都是常態。家長都在工作,孩子就是大的帶小的,沒人天天盯著孩子。
至于學習,更無所謂了,直接把孩子交給老師,讓老師狠狠打,不行就說明不是讀書的料兒,讀不下去,去干農活或者學門技術也能活。
後來,我爸爸沒考上高中,直接職高畢業后,十六七就去供銷社工作了。
當年流行起《少林寺》,電影院都擠爆了,好多人尿到褲襠里,都得把片子看完,票搶不到。
張家老二知道我爸爸有門路,就央求我爸給他弄幾張票。
我爸爸是一個典型e人,社交恐怖分子。這種舉手之勞,直接給他弄了,讓他下午來拿。
結果,下午人沒來。我爸還納悶,想來票別浪費了,就擠進去又看了一場少林寺。
事后去清河喝酒,聽張家人說起張老二死了。他爸爸讓張老二去鄉里給姐夫送胡麻油,開的是單位上的長把兒手扶拖拉機。
張老二不樂意,說是自己下午有事。他爸爸就給他一耳光,說有事咋了,開快點不就行了。
那玩意賊不好開,張老二又開得快,路上撞樹上,長把兒把人摔出去,直接摔河里了。
之后找人,是沿著河一直找,在下游金川峽水庫里找到的尸體。
我爸倒也實誠,他一五一十給張家人說,應該是急著到我這里拿票呢。
張家人也不介意,只是拉著我爸灌酒。
之后我爸去給張老二上了香,這事就結束了。
我打小就是聽我爸講這些零碎故事長大的。
我爸爸的話是,那時候,糧少,人多,吃苦,命賤,但人不多事。
他們同學聚會,每次都要聊那些逝者,集體往地上澆一杯酒,像是某種儀式。
但往事如煙,一切好像都能輕飄飄過了。以至于我爸爸都把這些當趣聞,講給我來聽。
60年代離我也就是一代人,中國發展太快了,以至于30年的變化,都足以讓不久之前的人事成為迥異于當下的傳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