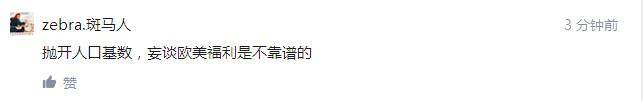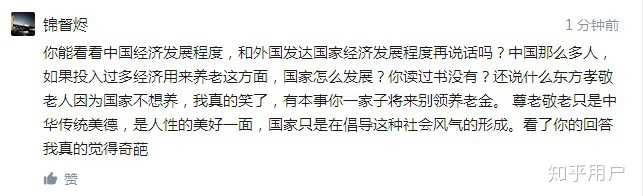我父親注定是一個要孤獨慘死的人。他有私生子,情人無數。他是一個稍有油水的庫房總管,在外揮金如土,回了家就哭窮。他給情人買的大衣,3000元起,情人女兒和我同歲,大學聯考成箱地送腦白金,喝不完。零幾年時候液晶電視等獎品直接送情人家。直到19年,我在老家還能翻出來買腦白金送的圓珠筆。而我和我姐穿衣服都是100元出頭,或者穿親戚送的衣服。我媽過年去他單位鬧,他拉不下臉,才肯給1000元過年費。最囂張的時候,恬不知恥給我1元壓歲錢,說家里窮,這錢給你去創業,等你長大孝敬我。我媽是個很正直的人,婚變讓她傷心憔悴,病了,高燒在床,奄奄一息,幼小的我陪在她身邊,很害怕她死了。我爸在另一個屋抽煙看電視。我媽在家跌倒,頭卡在電視柜和衣柜中間,呼救了1分鐘,我爸在另一個屋關著門看電視,最后她自己慢慢爬起來。
我出去洗個澡,我們鎮上澡堂的老闆娘都是他的姘頭。他踐踏家庭,從剛開始的偷偷摸摸,到后邊肆無忌憚,家里酒店飯店洗浴中心的打火機不計其數。家庭已經阻止不了他,他覺得家庭是個牢籠。他從偷情發展到帶著情人在街上打我媽,人格開始變態。然而他白天浪蕩瀟灑,回家就無比空虛悔恨,性格陰晴不定,酗酒,我媽和他要撫養費時,對我媽動了兩次手。最厲害的時候,他喝醉酒回來,聽到他上樓的聲音。我們全家都要飛快躲入另一個屋子,鎖好門,屏住氣面面相覷不說話。端個飯盆,坐在電腦桌前玩象棋,鼠標漂移失靈,就摔打鼠標。此時他的心態已經是個預備殺人犯,稍有觸犯很可能就引發血濺滿門。這樣的日子持續了我整個少年時代。好在我媽學識高,收入高,是個能隱忍的女強人,保護著我和姐姐長大,我上大學時他倆離婚。
她無數次地和我們講:「天下沒有熬不過去的事,做事情要隱忍,美好的日子在后邊」離開他我們家過的很舒服,我媽在縣城買了三套房,現在我一年能賺30多萬,我姐在市里有車有房。他落魄回到農村,在老家住著。他這個不學無術的人,對于我們家庭來說只是一個痛苦的回憶。我和姐姐都做好了準備和他斷絕關系。時間到了2019,現在他老了,變得無害,脾氣下來了,女人們也不跟他鬼混了,他農村那一幫廢物家人又勸我媽回去。之前他拋妻棄子,家庭暴力,酗酒賭博的事情,他們都明明白白,卻從來沒人管。這時候在他們眼里都是小事,都比不過他們農村的孝道和所謂的「大局」。其實呢,就是他把自己的錢敗光了,農村現在要蓋房子,他們缺錢,就唆使我媽回去出錢給他們家蓋房子,而他們的理由永遠是為了下一代也就是我的好。
我上大學前只知道我爸爸是個酗酒的混蛋,我媽瞞了我很久,上大學之后才知道他之前所有的齷齪事。我很認真考慮過殺掉他,買好了票,準備坐火車回去一刀一刀殺掉他。後來想了想我的母親,放棄了。我們家需要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而不是我一怒逞恩仇。每一次過年,他都一個人在寒冷的院子里孤單踱步。一個人點篝火,一個人貼對聯,一個人放炮。沒有人管他。我的叔叔可憐他,淚流滿面讓我回去看望他,我也只會嬉皮笑臉應付一下。即使偶爾回去,他能得到的只是我那冷酷冰霜的臉。孝敬老人的錢我不會給的,一分錢都沒有,他從自己的錢包里掏錢,我用他的錢去孝敬老人。我爺爺抓著我的手,和我說,你以后要管你爸爸啊,我們倆死了這個院子就只有他了,我笑臉逢迎的說好的沒問題,我爸在一旁默不作聲。
哈哈,諷刺的是,我兒童時最初的記憶,就是夏天坐在老家的院子里,眼巴巴地望著黑洞洞的大門,問爺爺:「我爸爸什麼時候回來看我?」我人生的最高目標之一就是在以后漫長的日子里孤立他、折磨他,讓他痛苦的死去。
第一次回答兩天以后,寫在下邊的話。
這些年我走上了社會,閃爍的三里屯,高壓的生活讓我麻木。26歲的我每天要比同齡人忙很多,一周7日無休。在IT公司有了自己的股份。
偶爾回想往事,十年前那個遙遠城鎮小家庭從富變窮,期間發生的無數事,讓我產生了時代的錯亂感和記憶的破滅感。
我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,日后可以用在法庭上,主要是用于家族內部控訴時,避免我無力陳述:
他的第一個情人是我家對門的鄰居。
我媽生我的時候,她正好也生了個兒子。
她過來串門的時候,看到我9斤,極其嫉妒,把我抱起來再假裝不小心摔在床上。
她是個長舌婦,說漏了一句:「這個小胖子皮膚真白!屁股真大,和他爸一樣!」
我媽聽到這句話,察覺到他兩之間的奸情。
他的第二個情人在農村,中年時候已經宮頸癌死掉。
我媽說,我爸和這個女人的兒子,和我長得一模一樣,20多歲,高大強壯,但是很蠢。高中時輟學了。在一個修理鋪打工。
因為這個私生子,我媽發了瘋,托人找黑社會抓奸,拍了錄像,逼他寫了保證書。
第三個情人的丈夫知道他老婆這樁奸情,但是暗允她老婆憑借這個撈錢(我家當時挺有錢)。她的女兒(腦白金女兒)嘴甜,也稱呼我爸為爸爸,她在太原理工大學讀書,現在已經畢業了。
我爸在汽車站買了小房子,就像《廢都》里的求缺屋,作為他們茍且的地方。
他平時回老家特別勤快,因為老家就在汽車站旁。然而他在搞時間差,每次回去,先和情人見面,然后再回老家。
和家人哭訴我媽榨干了他的錢,把他趕了出來,家庭逼迫得他沒辦法活下去。老家的人看他這麼落魄,因此集體怨恨我媽,讓我爸停止上交工資卡。我媽悲憤,唾棄他們的虛偽。雙方停止了節假、婚慶來往。
我媽知道這個女人之后,就和他離婚了,兩個孩子歸女方,男人拿房子,女方拿錢。但是約定我上大學之前不公開,男方必須供養孩子直到大學畢業。
諷刺的是,這個男人口口聲聲說他為了家盡心盡力。2005年到2015這10年,我們家的家居增加列表為:一台彩電,一個立柜,一個單人沙發,一台電腦。
我自己的錯覺就是我爸1998年一個月賺2000。
到了2010年,怎麼還是2000呢?
這是世界上最會編故事的男人。
第三個情人是澡堂的老闆娘,他每次帶我洗澡,我都能看到這位高個子的長髮女人。她有著一股交際花特有的溫柔氣質,和我爸說話時,那明亮奪魄的眼神充滿了曖昧。她在澡堂后邊有一個小屋子,這屋子必定發生過見不得人的故事。
這個女人我媽之前沒告訴我,我自己看出來的,長大后我親口問了一次,確認了我不是瞎猜。
第四個我不知道她的底細,是個外地女人,經我爸一個商人狗友介紹,給他倆提供了住房。商人因此借機套利不少。
當時我父母同房分居,我爸大搖大擺帶著她在街上亂逛。小鎮認識我媽的人對他怒目而視,嘲笑他:「老三這是在逛街呢!」
這個女人很勢利狂妄,打電話給我媽挑戰。
我媽和她在電話里面對罵。不久,我爸就沖回了家要教訓我媽。我媽和我姐拿出了刀和改錐,說,今天我們三個魚死網破,你有種把那個女人也叫來,不能讓她走。我爸慫人本質暴露,就罵罵咧咧地走了。
我在上高中,這是我知道的第一個女人,我知道事情后給我爸打電話:「你再這麼折騰,我就殺了你和那個婊子,把你們的腦袋割下來,你試試我敢不敢」。
這個慫人,非得等到自己的孩子和他眼紅,他才感到害怕,收斂。
就這樣,我媽還得經常上門和他要生活費,他從來不會主動給的。
他還記錄了每次因支付我學費、月生活費而在ATM取款的流水。寫在一張長條紙上,我在他的辦公室發現了,他的用意我不清楚。這事讓我冷笑。
第五個,第六個...還有多少呢,我不清楚。
小時候,我爸在家發怒的時候,我姐哭著勸他說:「爸爸,我的同學故意和我說,你外邊養女人,我和她們在一起走路,我的臉發燙,我好丟人!」
我爸怒罵她:「給你再找個阿姨你覺得不好!?老子我找的都是極品!」
上大學后,仔細回味了這些年我家的畸形,我母親的痛苦,我姐姐委屈的眼淚。
失衡的復仇心滋生,暴力的種子發芽,每日每夜睡不著。
買了刀片壓在枕頭下,夜晚躺在床上,盯著潔白的墻壁。那種感覺就像躺在奧斯維辛那一尺見寬的棺材里,熬得人頭疼發狂。身邊有無數的冤魂,恐怖的魔鬼,唆使我站起來,回家弒父。
可是殺掉他,我也就完了。我的遠大前程,母親的關愛、這麼多年的奮斗、心血就白費了......淚水無聲地留下來,肌肉緊繃著,身體在顫抖,嘲笑我這個20歲無力保衛家庭的大孩子。
一個人在北京的雨夜里走路,雨打在頭上,我很享受。每天穿梭在自習室和宿舍之間。仇恨寫入了我的DNA,仇恨驅使我變得更強。仇恨讓人上癮,讓我通宵達旦地學習、工作。
一個人的時候,總是習慣性地沉默思考。而在同學面前,總是一副高昂的姿態。
連年累月的家庭斗爭,是最真實的教材。
從這本血淚教材里,我學到了到親情的價值和社會的殘酷,學到了怎樣無情地斗爭,學到了堅強沉默。為了生存,為了錢,為了自己的安全感,為了自己愛的人。不顧一切地賺錢,成為辛德勒那樣縝密的社會人。
喜歡上了索爾仁尼琴,余華,路遙,柯艾略。憎惡父權和威權。我一次次告誡自己,要把握自己,自己主宰自己的生命。可是走在街上,看到男人欺侮女人,傷害兒童,處事不驚的我又會發狂,失去理智。
十年前的家仿佛是個地獄,十年后父親變老了。凌厲的眼神變得渾濁,體型發福,神態遲鈍,性格溫和了。
老人知道自己年輕時犯過的錯,在我面前變得溫順,像我養過的那條遲暮老狗一樣低眉順眼。沒有一個舊相好真心實意愿意跟他。他現在依舊每日穿梭在那條路上,過去是隱秘的偷情之路,現在是孤獨的回家之路。
主動打電話,關心我在干什麼,希望我能回家吃他做的面。我只給他30秒通話時間,哦哦幾聲就掛了。
我的母親一輩子沒有再找男人。離開了父親,她逐漸恢復了活力,每天奔波在包頭,大同的洗煤廠,還有那些男人不敢進入的深山黑煤礦幫人算賬。洗煤廠全是藏獒巨犬。後來在家帶小孩,每天在菜市場、幼兒園、物業交費處忙碌,家里永遠光明幾凈,玻璃一塵不染。
她說:「我這輩子可惜了,最可惜的是你爸爸,他不像個男人。我如果是他,是一個男人,咱們家不至于此。」
過年給我買的衣服太肥,她們舍不得浪費錢,要我寄回老家給父親穿。我出門轉手就把這些衣服扔進了垃圾堆。
寫不下去了,我寫的這些人不喜歡上網,估計也看不到,我把這兒當個樹洞吧。
即使看到了,知道我是誰。我只想和我提到的這些仇人說,你們這些人,我保證,以后一個一個都脫不了我手,不得好死。
2020年:
生活還在繼續,日子過得比以前好多了。因為老吃魚變胖了。去年HK暴亂,很多奢侈品門店業績不好,開始走線上,因為這兩年一直做電商,靠這個有了業績,收入顯著提高。老姐搬了新家,我資助了裝修錢。老媽熱衷于減肥,我贊助了會員費。
因為疫情沒有帶家人去泰國玩有點遺憾。
前年開始每年給家里10萬塊,逐年增加。我媽不要,堅持給她。不為別的,就為了和家里表明我過的很好,不但能養活自己,還要養活家人,家里還有男人。我媽說都給我存起來,留著結婚用。我表示錢還能賺,這錢留給她旅游也好,做什麼都行,就是別給我,不然沒有賺錢動力。
老家那里,最近因為我爸老了,孤單。親戚們依舊攛掇我媽回去過日子,搞得像是我媽任性離家出走一樣。勸和理由永遠有:1. 孩子要結婚,父母離婚對孩子不利。2.都是過去的事情了,退一步海闊天空,老了總有人互相照看。我媽因為尊嚴問題拒絕了他們。
完全沒有先解決我爸的歷史問題,給我媽一個公正的道歉和地位。反正在他們心里女人大概就應該是軟弱可欺,忍辱負重的,我媽到底怎麼想的不重要。
這是他們的愚見,過去他們也是一直這麼愚蠢地勸女人大度,幫著拆我們家。我爸呢,這個還是躲在家里一聲不吭。
我記得大學回家,他還和我說:「爸爸有難處啊」。我工作之后想了很久,實在無法明白他的難處在哪。親戚們和我說,你爸爸養你姐弟不容易。我感覺很可笑,看來養幾個情人比養兩個穿百家衣的小孩還容易吧。或許他們不知詳情,把我爸給女人們花的錢算到我頭上了?
家里的院子修好了,他指著一件側房和我說:「這是給你結婚留著的」。我看了一眼說:「嗯,不錯」。大家紛紛說我爸不容易。
我叔暗示我姐,問我爸的養老問題,如果父母不能復合,給我爸找老伴是否可行。我姐說:「我當然希望我爸以后有人照料。但是如果他領別的女人回家,我擔心我弟弟發起火來收拾不了」。
這事他們就不再問了。
這些年,我的思想不如前幾年那麼偏激,仇恨一切。但是我個人對我爸的態度從來沒變過,工作以后沒有給過他一分錢,他蓋房我從來不問不參與。回老家看爺爺奶奶,看他用一個很舊很卡的vivo刷抖音。因為流量少,還要去蹭隔壁的網。動了下惻隱之心。以我現在的能力,我能讓他用最好的手機,住最好的房子,還用這麼苦地勞動受罪嗎?但是我最終什麼都沒表示。畢竟我家最難的時候,這個人什麼也沒干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