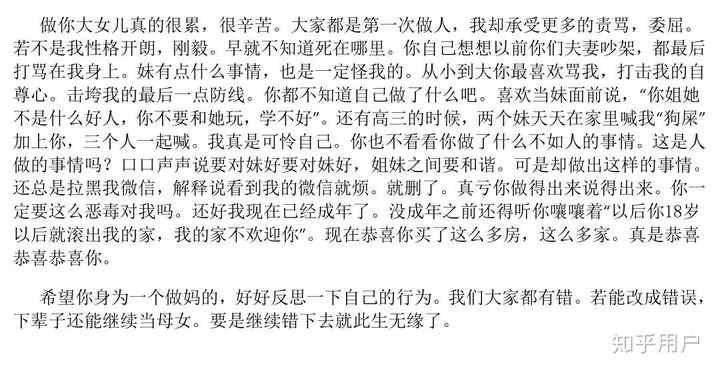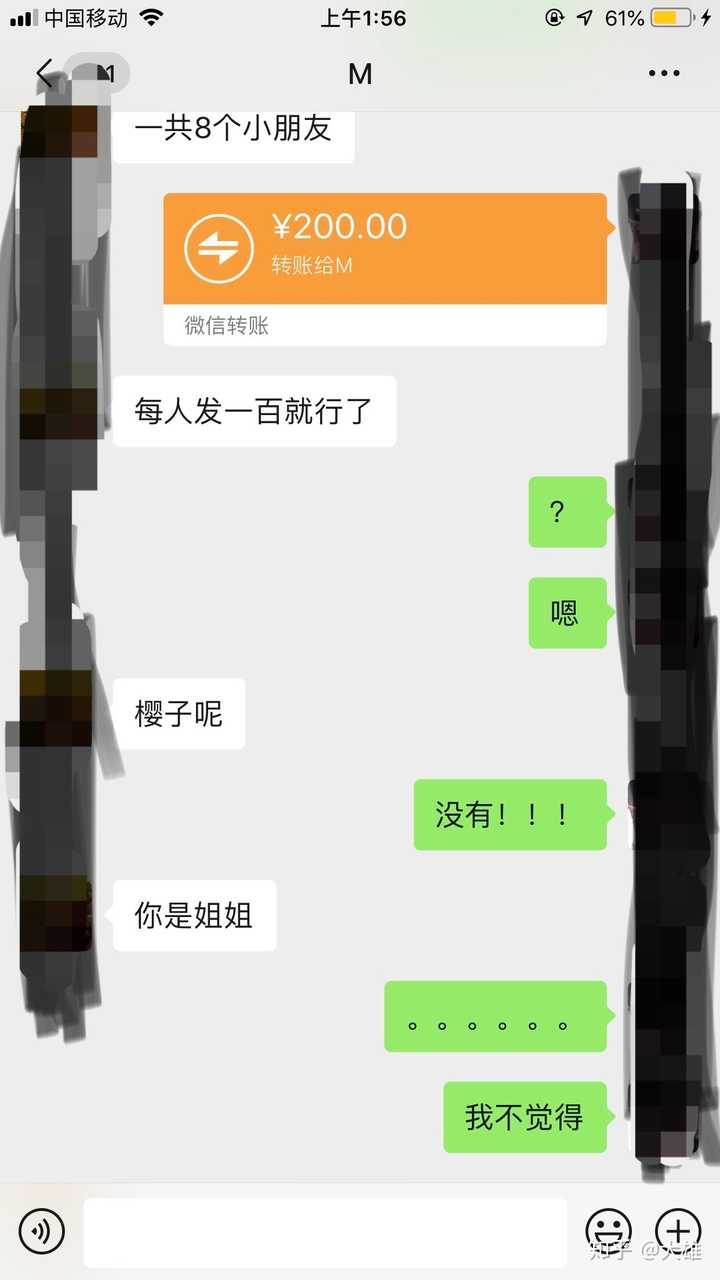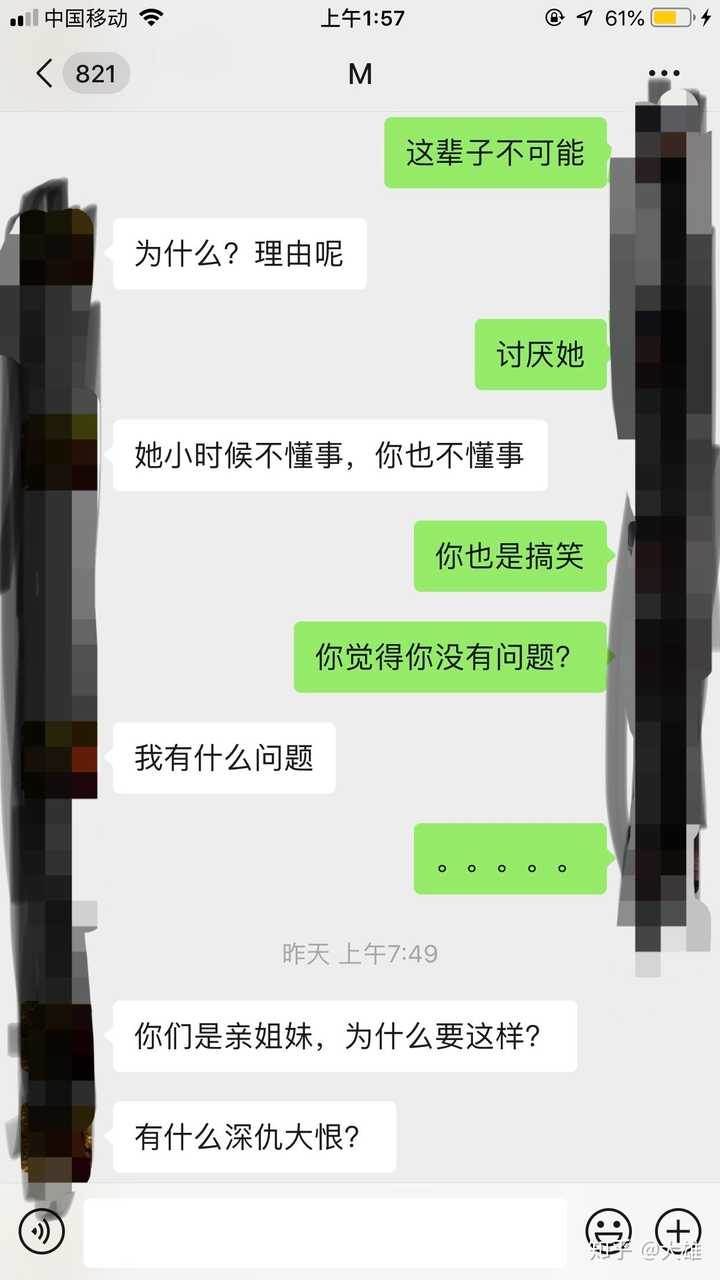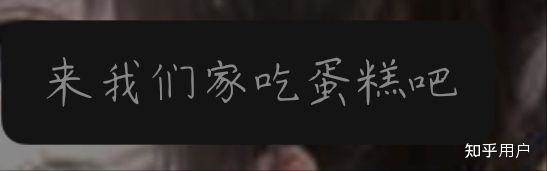在那個被侵犯后又活著被肢解的晚上,我口中一聲聲的喊著媽媽。而我的媽媽在溫暖明亮的家里,為她心愛的大女兒梳妝。生前死后,我都是那個家中最透明的存在。
1
我死后當天,姐姐的婚禮照常舉行。
她穿著婚紗,嫁給了我的男朋友。
我媽打了好幾通電話沒人接,慍怒地罵我白眼狼。
弟弟發消息斥責:「你就這麼小心眼,兩年前的事情記到現在?」
一向寡言的爸爸冷著臉說:「你告訴她,今天不回家,我們就當沒生過這個女兒。」
他們并不是真的希望我回家,只是不希望姐姐的婚禮因為缺少我的祝福,而不夠完美。
可是,我已經死了。
從很小的時候起,我就知道,我在這個家里不討人喜歡。
媽媽去外地出差,回來時帶了兩個新款玩具,分給了許澤和許嬌。
分完她就要走,卻被我攔住,細聲細氣地提醒:「媽媽,還有我。
」
「你也要?」
我媽皺著眉,不耐煩地說,「很貴,我身上帶的錢不夠,沒算你的。」
那時候我才五歲,但已經對別人的情緒有了隱約感知。
何況,那個人是我的親生母親。
而現在。
在姐姐的婚禮現場,我媽與幾個親戚客套完,走到角落,背過身,一遍又一遍地撥著我的電話。
始終沒有人接。
到第三個的時候,直接被掛斷了。
她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,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:「許桃,我是你媽!」
許澤走過來,安撫地拍著她的后背:
「媽,你別生氣,為了許桃不值得。你還不知道嗎,她就那樣。」
我媽惱怒又委屈的情緒,終于在她最疼愛的小兒子那里有了出口。
「你們三個孩子,我在許桃身上付出的心血最多,當初生她的時候明明是龍鳳胎,就連醫生都說她是搶了你哥哥的營養才活下來……」
這句話,從小到大,我早已聽她重復了無數遍。
到最后,往往是我被懲罰一頓,鎖在房間里,看著他們一家四口出門散心。
「媽你別生氣,放心,今天就算是綁我也要給她綁回來。」
許澤安撫好我媽,轉頭給我發了很多條微信。
「許桃,你最好在一個小時內出現。」
「你怎麼這麼自私啊,明知道媽心臟不好,還要氣她。」
「一個男人也值得你記恨到今天,何況姐姐不也是你的姐姐嗎?」
發出這句話后,他的手指在鍵盤上頓住。
幾秒后,他收起手機,轉頭去幫著招呼客人了。
是啊,連他自己都不相信吧。
許嬌是他的好姐姐,是我爸媽的好女兒。
怎麼會是我的姐姐呢?
2
我往樓上飄過去,看到許嬌坐在化妝間里。
化妝師正為她補上微微花掉的眼妝。
她攥著爸爸的手,眼睛里水光朦朧:
「爸,桃桃真的不來了嗎?她是我妹妹,我最重要的日子,真的希望能得到她的祝福。」
在我面前從來嚴厲到冷漠的爸爸,拍著她的肩膀,輕聲安撫:
「不會的,我讓阿澤聯系她,不會讓你留下任何遺憾。」
他在走廊里找到許澤,冷著臉說:「你告訴許桃,今天不過來,我們全當沒生過這個女兒。」
「爸,她根本不回我的消息,連媽打電話她都不接。」
許澤咬牙切齒地說著,「我就知道,像她這種人,天生沒良心。一開始答應我們,就是故意給我們希望,想讓姐姐最重要的日子不痛快。」
今天是許嬌最重要的日子。
她就要穿著婚紗,嫁給和她戀愛兩年的男人,宋斐。
兩年前,我把宋斐帶回家時,許嬌對她一見鐘情。
我至今記得,她看到宋斐的一瞬間,眼睛都亮了,晚上找了個借口,約我出去散步。
她給我買了杯奶茶,挽著我手臂晃啊晃:
「桃桃,我真的好喜歡宋斐這種類型的男生,你這麼優秀,肯定能找到更好的,就把宋斐讓給我好不好?」
我拒絕了。
可回學校后不久,宋斐就向我提了分手。
我反復追問理由,他大概是被我弄煩了,一把甩開我的手。
我跌坐在地上,掌心被粗糲的地面磨破,傳來刺痛。
而他無動于衷,只是用厭惡的眼神看著我。
「還想瞞著我嗎?連你家里人都看不下去,告訴我了。」
某個我媽忽然喊我出門和她買菜的早上。
我的弟弟,許澤,拉著宋斐,告訴了他一些關于我的「真相。」
人品敗壞,偷家里的錢,霸凌同學。
亂搞男女關系,大學的時候打過胎。
說到最后,正義的許澤嘆了口氣:
「許桃是我的姐姐,我很想向著她,可是……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你掉進火坑里。
」
蹭破皮的掌心還在發痛,我坐在地上,仰頭看著宋斐,聽著他口中復述的事情經過。
最后一個字音落幕,我忽然笑起來。
他皺著眉:「你還想辯解什麼嗎?」
我搖搖頭,笑著說:「他們說的都對。」
宋斐對我,本也沒有多麼深重的感情,何況跟他講我有多麼壞的,是我的家人。
我至親至愛的,家人。
我活著的時候,他們無人關心。
死后當然也無人知曉。
3
說話間,宋斐來了。
穿著西裝,特意弄了髮型,顯得人更加俊俏。
他親了親許嬌的臉頰,柔聲問:「許桃還是沒到嗎?」
許嬌含著眼淚點點頭。
「算了,別管她了。」宋斐臉色一沉,「這種人,來了也會弄臟我們的婚禮。嬌嬌,今天你是新娘子,不要為不值得的人掉眼淚。」
許嬌順勢摟住他的脖子,仰著臉,神色難過:「不管怎麼說,桃桃都是我的妹妹。
」
她的表情看上去,始終真心實意。
就像三年前,作為優秀畢業生,學校提出,希望畢業典禮那天,我爸媽能夠到場,上台說兩句,也方便學校拍照宣傳。
我反復組織措辭,把電話打回家,小心翼翼地提出請求。
我媽答應了。
可就在當天早上,她打來電話,告訴我她和我爸來不了了。
「嬌嬌生病了,把她一個人扔在家里我們不放心。」
視頻里,許嬌頂著一張面色微白的臉,歉意地看著我:
「對不起桃桃,我身體有些不舒服……你一直都很獨立,爸媽不去,你也一定可以處理好的。」
「桃桃,畢業快樂。」
畢業快樂。
我怎麼會快樂呢。
在我畢業典禮這天,我跟老師道歉,跟學院道歉,跟活動處的教職工道歉。
路過攝像機時,恰好聽到有人在抱怨:
「流程都排練好了,這下又要重新弄。
什麼垃圾,就這還優秀畢業生。」
典禮結束時,我拿出手機,恰好看到許嬌發了條朋友圈。
「其實只是場小感冒,但爸媽都很關心地照顧我,生活中的小確幸~」
配圖是他們一家三口的合照。
背景是在許嬌的臥室。
他們甚至連醫院都沒去。
真是,好嚴重的病啊。
4
宴會廳內放著悠揚的鋼琴曲。
許嬌穿著長長的魚尾婚紗,抱著一大捧白玫瑰走向宋斐。
爸媽致辭之后,就輪到許澤。

他站在台上,玩笑地沖宋斐揮了揮拳頭:
「我就這麼一個姐姐,是全家人的寶貝,你要敢對她不好,全家人都饒不了你。」
宋斐凝視著許嬌的臉,語氣深情至極:「我可舍不得。」
台下鼓掌聲響起。
台上溫馨一片。
我的靈魂站在台邊的花束上,木然地看著他們。
我以為自己會心痛。
但可能是死前,已經把這一生的疼痛都經歷完了。
我只是冷眼旁觀這一切,心里空空洞洞,好像有風吹過。
某張桌子前,有人在竊竊私語:「誒,我記得許家有三個孩子,怎麼許澤說他只有一個姐姐?」
「還不是他家那個二女兒許桃,嘖,學習好有什麼用,做人最要緊的是人品……」
托我爸媽的福。
我在兩邊親戚那里,也是惡名遠揚。
其實小時候,有一個姑姑對我還是不錯的。
過年時來走親戚,她送了我一個毛絨小海豚的玩具。
只有我一個人有,許澤和許嬌都沒有。
許澤霸道慣了,讓我給他玩,我不肯,他就直接拿剪刀把海豚剪碎了。
沒過多久,姑姑去而復返,來拿她忘記拿走的圍巾,正好看到滿地碎片。
為了維護她心愛的小兒子的名聲,我媽告訴姑姑:
「桃桃不喜歡這玩具,非要拿剪刀剪碎了,說是不想看見。」
姑姑的臉色一下就變了,後來每次來走親戚,她連給紅包都略過我。
這事之后,我媽大概是有點愧疚,對我好過一段時間。
但很快也就消散了。
在我們家,爸媽的偏愛有著明確的分工。
許嬌出生那年,我爸的生意有了很大的起色。
他認為這是許嬌帶來的好運氣,所以最寵她。
而我媽,最疼愛許澤,因為這是她生了三個才盼到的小兒子。
至于我。
出生后白白胖胖,我的同胞哥哥,卻連 24 小時都沒挺過去。
他們都覺得我不吉利。
小時候,我總是想不明白。
為什麼許澤和許嬌想吃什麼,第二天餐桌上就有什麼。
而我明明海鮮過敏,我過生日的時候,只是因為許嬌說了一句想吃螃蟹,我爸就把地方定在了海鮮餐廳。
我十二歲那年,隔壁縣地震。
當時全家人正在家午睡,爸媽想也沒想,一個人抱許澤,一個人抱許嬌。
我跌跌撞撞地往樓下跑,看著搖晃的天花板,哭得聲嘶力竭。
但沒有人會來救我。
十二歲的時候是這樣。
我被那個司機掐著喉嚨,拖到荒無人煙的山下樹林里時,也是這樣。
5
下午,婚禮圓滿落幕。
送走了客人之后,我爸立馬沉下臉,讓我媽繼續給我打電話。
許嬌眼圈紅紅的,眼尾貼著的幾顆水鉆折射淚光,她握著爸爸的手,語氣善解人意:「算了吧,爸。」
「桃桃還是個孩子,可能是在鬧小孩子脾氣。
我畢竟是她姐姐,不該和她計較這些。」
果然,我爸眼中掠過一絲心疼。
許澤不滿地說:「姐,你就是把她想得太好了。你把她當妹妹,她有把你當過姐姐嗎?」
許嬌咬著嘴唇,看上去幾乎快哭了。
我站在旁邊,看著她,只覺得無比諷刺。
許嬌永遠都是這樣。
家里人對她偏愛已經明顯到不能再明顯的地步,可她仍然覺得不夠。
我知道,那是因為她憎恨我。
其實最開始,我媽雖然不喜歡我,但對我沒那麼差。
我過生日的時候,她也會拎回來一個蛋糕給我慶祝。
只是點起蠟燭,我正要許愿,許嬌突然哭了。
她擦掉眼淚,故作堅強地笑了笑:
「沒什麼,只是突然想起,本來今天過生日的,應該是兩個人。」
一句話,說得我媽變了臉色。
我雙手合十,正要許愿,她忽然粗暴地拔掉蠟燭:
「吃吃吃,就知道吃!許桃,你知不知道你哥哥就是因為你才死的?你有沒有心?」
我被嚇到,呆呆地看著她。
我媽更加生氣,直接把蛋糕掃進了垃圾桶。
她進臥室后,我滿眼是淚地看向許嬌。
沒有其他人了,她終于向我袒露真實的情緒。
十歲的許嬌,臉上仍然帶著溫柔的笑意,吐出的話卻像淬了毒的刀鋒。
「許桃,你為什麼要出生呢?」
她用溫熱的指尖拂過我的臉,然后忽然狠狠擰了一把,
「本來爸爸媽媽只愛我一個人,現在你分走了他們的愛。你就應該和弟弟一起死。」
我始終不明白,她這樣恨我。
可偏偏許澤出生后,她又對他很好。
我大學聯考那年,許澤即將初三。
最關鍵的一年,但我爸的生意忙到走不開,我媽也在升職的關鍵時期。
我媽要求我,報本地的大學,平時方便照顧許澤。
我沒有答應。
她用冷冰冰的眼神看著我:「許桃,家里什麼情況,你不知道嗎?你怎麼這麼不懂事?」
我去上學之后。
已經二十二歲的許嬌突然要學鋼琴。
我媽叫人扔掉了我的床和衣柜,把我的衣服打包丟進雜物間。
我的臥室,變成了許嬌的鋼琴房。
她在朋友圈發了一條視頻,是她坐在新買的昂貴鋼琴前。
陽光灑落。
而她笑容恬靜。
我打回電話,我媽還在為我不聽她的話而生氣,嗓音很冷淡:
「反正你現在翅膀硬了,我說什麼都不聽,這個家你也不打算回,留著房間干什麼?」
許嬌接過電話:「桃桃,你別惹媽媽生氣了好不好?等你回家,就和我睡一個房間,家里不會讓你沒地方住的。」
哪怕她已經極力掩飾,嗓音里還是帶著一點笑意。
我剛離開一個月,她就迫不及待地想把我趕出這個家。
而我媽選擇了默許,和縱容。

6
下午,許嬌跟著宋斐回了他們的新家。
而我,跟在我爸媽和許澤身后。
許澤開著車,爸媽坐在后座。
空蕩蕩的副駕,一直以來都是留給許嬌的。
我坐在上面,聽著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我的罪過。
「她就這麼恨我,恨這個家,連她姐姐的婚禮都不愿意回來參加。」
我媽疲倦地靠在我爸肩膀上,「我覺得自己的教育真的很失敗。」
我爸心疼地拍了拍她:「養不熟的白眼狼,不值得你為她費神。」
我扭過頭去,仔仔細細地觀察他們的表情。
試圖從上面找到哪怕一絲關心。
可是沒有。
我突然的失聯,只讓他們覺得惱怒和憎惡。
沒有一個人,有一秒鐘懷疑過。
我是不是,出事了。
明明是一道靈魂,可我竟然還會流淚。
我一邊流眼淚,一邊笑著問:「媽媽,你真的真的,有愛過我嗎?」
「這麼恨我,為什麼要生下我?」
同樣的問題,很久之前我也問過一次。
那時我初三,學習很緊張的一年。
我爸在外地談業務,許澤年紀還小,許嬌剛上大一。
我媽得了腎結石,是我每天學校醫院兩頭跑地照顧她,累瘦了一大圈。
我媽好像也有動容,那個月給了我比許澤更多的零花錢。
遇上鄰居,她跟人家夸了好幾遍,說我懂事,孝順。
我被同學欺負,她甚至去了趟學校,為我出頭。
好像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發展。
直到那天下午,我們一起過馬路時,她不知道怎麼,挽住了我的手。
這樣母女間的親昵,對我來說實在太過陌生。
我幾乎是下意識地,揮開了她的手,以至于她踉蹌著后退了兩步。
正值黃昏。
綠燈轉紅。
一輛小轎車呼嘯著從我們身邊擦過。
我媽看我的眼神又慢慢變了。
是一種我很熟悉的冷淡。
她繃著臉,淡淡地說:「果然是養不熟的白眼狼。」
那天晚上,我幾乎被懊悔和茫然的不知所措吞沒,拿圓規在自己胳膊上扎出好幾個窟窿。
連疼痛也不能緩解我心里橫沖直撞的絕望和焦躁。
最后我走進我媽的房間,問她:「媽媽,既然不愛我,為什麼要生下我?」
我媽閉著眼睛,一言不發。
可我知道她沒睡。
我生前她都不屑于回答。
如今死了,她聽不到,更不會回應我。
7
晚飯過后,許澤又給我的手機打了個電話。
這一次,居然被接了。
他滿腔怒火終于有了發泄的出口:
「許桃!!你是畜生嗎?姐姐結婚你不回家,惹爸媽傷心,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了不起,耍我們很好玩啊?」
安靜片刻。
電話那頭傳來一道嘶啞的男聲。
「我是她男朋友。」
「她說,你們一家人都挺噁心的,不會回去見你們。」
「別再打來了。」
電話掛斷。
許澤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,片刻后,忽然暴怒地踢翻椅子,罵了句臟話。
可我已經渾身僵硬,失去了全部的力氣。
在那道聲音響起的一瞬間。
我就被強行拖進那段回憶里。
我死前,因為加班錯過了最后一班高鐵。
只能打車去汽車站。
司機是個面色蒼白的年輕男人,眼神有些陰沉。
有些眼熟,但我的大腦實在困倦到極點,抱著東西,靠著車窗休息。
一開始,一切都很正常。
他像所有司機那樣和我閑聊了幾句。
這時候,許嬌突然打來了電話。
身為準新娘的她,連婚禮前夜,都不忘來刺激我一下。
「桃桃,明天我就要嫁給宋斐了,還真是有點激動得睡不著。」
她溫溫柔柔地說,「謝謝你帶他回家呀。」
我抿了抿唇,聲音里壓著怒火:
「許嬌,這種噁心話,這種骯臟手段,你還要玩多少次才會膩?」
她像是完全察覺不到。
語氣甚至更加輕快甜美。
「那就這麼說定了,明天婚禮你一定要來哦。」
我掛了電話,忍不住呼吸急促,胸膛劇烈起伏。
司機忽然出聲:「和家里人吵架了?」
我皺著眉抬起頭,才發現車不知道什麼時候,被開到了一片荒涼的野郊。
心臟一下子跳得極快,我強迫自己鎮定下來,問他:「你要多少錢?」
可他要的不是錢。
連續加班讓我疲倦至極,手腳發軟,根本躲不開一個年輕男人的力氣。
他捂著我的嘴,把我拖進小樹林。
夜晚的風很靜,月光柔和地灑落。
他一邊死死地掐著我的脖子,一邊用力地扇我耳光。
他說,賤女人,你是不是很后悔當初離開我。
你跟的那個有錢人憑什麼瞧不起我。
求饒啊,學狗叫啊,我就放過你。
可我甚至,不認識他。
你是誰。
你是誰。
他掐著我脖子的手忽然一松。
改為溫柔撫摸我的臉。
他說,我是你男人啊。
我總覺得,他好像并不全然陌生。
但就是想不起來在哪里見過。
我用盡全力掙扎,竟然真的摸到了手機。
快捷鍵會撥回最近的一通電話。
嘟嘟嘟。
兩聲響過。
許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掛斷。
那人發現了端倪,他殘忍地笑了一聲,把手機揣進口袋,然后掰斷了我右手的每一根手指。
他的口袋里,還裝著一把彈簧刀。
在我還有意識和知覺的時候,感受著刀刃切進左手手腕,被一點點拉扯,鋸下來。
刀尖劃開臉頰,撕下一張坑坑洼洼的臉皮。
他說:「賤人,看你還怎麼拿這張臉去勾引別人。」
8
我不記得我是痛死的,還是失血過多而死的。
只記得那天夜里,曠野的風。
呼嘯著吹過我血肉裸露的臉頰。
可能是人臨死前會想起一些美好的事情。
我茫茫然然,想到了五歲前。
為了生下許澤,我媽把我送到了鄉下。
那里原本只有年邁的外婆一個人住。
她是這個世界上對我最好的人。
給了我人生中全部的溫暖。
樹上最嫩的香椿尖兒,被她掐下來,用水燙過,炒雞蛋給我吃。
我媽打來電話,說許嬌想吃香椿了,可菜市場買不到。
外婆說,哎呀,今年雨水太少,香椿沒長出來呢。
掛了電話,頑皮的小老太太沖我眨眨眼睛,笑了。
我始終記得那天晚上彌漫在舌尖的滋味。
可是五歲那年,外婆病逝了。
許澤才一歲半,我媽就被迫將我接回家。
她因此看我很不順眼。
悄悄跟我爸說:「這孩子是不是真的有問題,怎麼連她外婆都克死了。」
我木然地看著她。
其實五歲的孩子,對生死還并不怎麼懂。
我只知道,世界上再也沒有人,會在幾個人中,堅定不移地選擇我。
我從此是永不被偏愛的小孩。

呼吸停滯的下一秒,我的靈魂被風拉扯著,從身體里飄出來。
我看到那個人從車的后備箱拎出一把斧頭,砍斷了我四肢連結的骨頭。
我看到星空下,火車疾馳千里,穿過靜悄悄的田野。
我看到高樓大廈的某一間,小女孩忽然從噩夢里驚醒,只哭喊一聲,就被沖進房間的爸媽摟進懷里,拍著背安撫。
最后的最后。
我看到許嬌打著呵欠從床上醒來,在我媽的催促下,洗漱完畢,換上出門紗。
我回來了。
死后,我還是回到了這個家。
參加了許嬌的婚禮。
9
那個男人強暴我,殺了我,肢解了我,還拿走了我的手機。
許澤沒有意識到這件事。
他只是冷著臉告訴爸爸:「許桃連我的電話都不肯接,只讓她男朋友告訴我,她嫌我們一家人噁心。」
我爸震怒。
拍著桌子罵我畜生。
似乎做生意的人,都比較迷信。
他喜歡許嬌,是因為她出生后,他的生意飛速發展,兩年資產就翻了幾倍。
那麼我出生后,他的廠子遭遇危機,險些破產。
他因此厭惡我,覺得我很晦氣,也在情理之中。
我爸掌握著家里的財政大權。
所以許嬌可以去讀十多萬一年的中外合資大學。
許澤可以補 700 塊一小時的課。
而我在一線城市讀大學,每個月一千兩百塊的生活費。
接下來幾天,我就待在這個家里。
冷眼看著他們正常生活。
看著我媽給許嬌打電話,問她回門時想吃些什麼。
許嬌撒嬌說,想吃海鮮。
我媽去早市買的時候,正好撞上我們兒時鄰居,帶著她女兒孟夢出來買菜。
孟夢和我是從小到大的同學,後來又進了一家公司。
算不上很親密的朋友,但至少比較相熟。
我媽羨慕地說:「養孟夢這種女兒真是貼心啊,一回來就幫著你買菜拎菜。
不像我們家那不懂事的許桃,她姐姐結婚都不回家,還找個男朋友來罵我們。」
「誒?」
孟夢有些驚訝,「阿姨,許桃沒有男朋友呀。」
我媽愣了愣,看著她。
「她在隔壁市場部,一直忙得要命,哪有時間交男朋友呀。」
她說,「而且許桃也很關心您呀,上個月發了獎金,我們去逛街,她還買了個金鐲子,說等她姐姐結婚的時候,回家就送給您。」
茫然無措的表情只從我媽臉上一閃而過,很快又褪成我熟悉的,冰冷的譏諷。
她說:「許桃就是在外人面前表現得好,你不知道她在家對我們是什麼態度。」
見狀,孟夢和她媽也不能再說什麼,客氣告別。
我媽買了很多許嬌愛吃的海鮮,拎著滿滿兩大兜東西回家。
站在門口,她掏出鑰匙要開門。
手機鈴聲響起。
是我的號碼。
「趙素女士嗎?我們抓到了一起惡性連環殺人案的犯罪嫌疑人,從他的身上搜出了這個手機,看備注,您應該是機主的母親。
」
「犯罪嫌疑人已經交代了埋尸地點,可以麻煩您和家人過來舟城一趟嗎?」
9
使用 App 查看完整內容
目前,該付費內容的完整版僅支持在 App 中查看
??App 內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