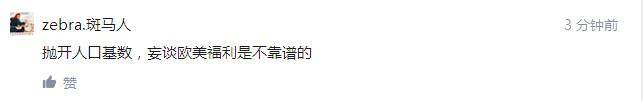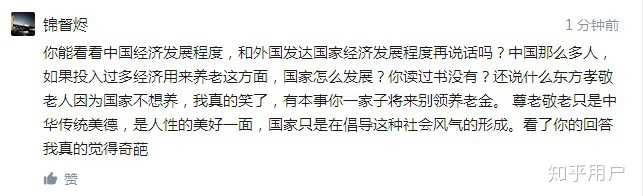我的病人「杠精」老張頭就是個「晚景悲涼」的例子。他因為自己的封建思想,逼走了女兒,寵壞了兒子,老伴也和他離心,最終孤獨地死在了酸臭的床上。
雨還在下,今年的吉林省降雨量極大,現在這場雨就已經下了16個小時沒有停,天空好像漏了一個窟窿,風不停地刮著,云也飛得很快。
老張頭已經死了有1個小時了,他好像被這場大雨帶走了。
5年前,我在父親的中醫館打雜,老張頭和他老伴兒也是在一個大雨天撐著一把傘進的屋。那時的老張頭身體羸弱但筋骨突出,厚實的手掌顯得強健有力,白色的長壽眉也略帶蒼勁,想象得到,倒退十年,他恐怕也算得上雄姿英發。
他進門就找了一個角落坐下了,和他老伴兒雙手緊握,佝僂著,咳嗽。
老太太不住地捶老張頭的后背。外面的雨還在下,混合著汽車的胎噪聲,直到我去詢問病情以前,他倆一直安靜地在角落里,一個咳一個捶。
「我們剛剛去的市醫院,我老頭有快半年休息不好了,現在干脆睡不著覺。醫院說年齡大了,最好別吃藥,靠中醫調理。」老太太邊捶邊對我說。
老張頭還在一邊急著要走,看得出來,他并不上心自己的病情,他可能覺得自己身體仍然不錯。
在診脈過后,我父親說老張頭屬「肝陽上擾」,失眠兼有性情急躁易怒、頭暈,且伴有胸脅脹痛。父親為老張頭記下病例,詢問下得知老張頭本名張林軍。
父親用馬丹陽十二針給他治療,讓我在一旁聽學,我至今沒背下來馬丹陽十二針,也不記得那天父親是怎麼扎的。但是我記得老張頭,因為扎針的時候他一直盯著我看,看得我心里發毛。
扎第一次針的末尾,老太太也說自己最近睡不著覺。同樣是睡不著,老太太和老張頭完全不一樣,她屬于心脾虧虛、脈多細弱。父親在開藥的時候,特意給老太太開的歸脾丸,給老張頭開的是逍遙丸和天王補心丸。
看見同樣的癥狀卻開了不同的藥,老張頭炸廟了:
「為什麼開兩種藥?」
「是不是騙我們老頭老太太不懂?」
「你多開藥能掙多少錢?」
他嘶吼的聲音極大,不像是一個一直睡不著覺的老人,瞪圓的眼睛里有點點黃斑和血絲,黃斑是火氣旺盛、暴躁脾氣使得肝病纏身的表征,血絲則證明他太長時間沒得到充分休息。父親很難給老張頭解釋他和他老伴兒的病情有什麼不一樣,于是老張頭就一直在那里喋喋不休,一旁的老伴兒也壓不住他。
「醫院中醫太貴,才來你們小診所!老子有錢我他媽去北京治,我來你這兒等著你騙我?開兩種藥什麼意思吧?!」老張頭一口咬死了,我家騙人。
父親擺了擺手,示意我:把藥拿回來,送人出去,不收錢了。
但老張頭那個架勢讓我有點害怕,我怕他推搡不過得抄起拐杖打我,更怕他順勢躺下——那幾年正是老人碰瓷的紅利期。
我退了一步,不知道想起來什麼了,就說了一句:「讓你兒子來,我們跟他解釋,我們開的藥沒錯,病不一樣,治法不一樣,你不能誣賴我們啊!」
老張頭聽完這句,把脖子縮了起來,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:「要是有兒子,至于我們兩個快死了的人來看病嗎?」
他的氣勢弱了下來,食指伸直,指了我三下,拉著老伴兒,抖了抖被淋濕的外套,扔下了30塊錢,推門又走進了雨幕。父親把錢撿了起來,也把他沒拿走的藥收了起來,一一向屋子里其他的病人微笑致歉。
在我看來,這老頭蠻橫,但扔下了診費,還至少體面。
這麼大雨天,連個陪護的人都沒有,他想必也有苦衷的。
父親扶著桌子,點了支煙,我相信他和我一樣,在回味老張頭給我們表演的鬧劇和他最后扔下的話,全屋子的人應該都在想——這句話太應景了,人在年老以后的生活,連下雨時都要忌憚腳下的青石板。
大概過去了半個月,老張頭沒再來過,我也好像要把他忘了,畢竟,脾氣大的病人也不止他一個。
一天下過雨后,我坐在中醫館門口看著街上人來人往。對過五金店的小孩把蘋果核兒扔在地上引逗螞蟻,商店的男人在門口支了一個燒烤攤在串肉。從一個胡同拐角,走出來一個身影,是老張頭的老伴兒。她向中醫館走了過來,我轉目不看她,因為不知道怎麼打招呼,但是她還是站在了我面前。
「同志,我上次來看過病,想把上次沒帶走的藥買走。」老太太有點羞怯地說。
同志?在現在,這是個很新奇的稱呼了,看她一字一句的認真模樣,我也慢慢想起來了。
「歸脾丸,逍遙丸,天王補心丸?」我問。
「好像是吧,不太記得了,同志你再幫我看看吧。」她邊說著話,邊摳著手,作為一個老年人,這種不好意思很難得,她可能生怕我說出來我記得他們——「你家老頭上次來要把我們家鋪子砸了」——諸如此類這種話。但是我沒有那麼不善良。
父親照常像接待新病人一樣為她號脈、詢問病情,她也字斟句酌地把老張頭的病情加在了自己身上。父親沒有點破,給她開了藥,也并沒有說,她其實不太需要逍遙丸和天王補心丸。
第三天的時候,老張頭就來了。不同于第一次的進門順序,這一次的老張頭是被老伴兒拉進屋子的,然后又如第一次一樣佝僂在角落里。
父親抻了好一會兒才去跟老張頭打招呼。一句沒問,就給他扎了馬丹陽十二穴,仍讓我在一邊學,我也照例背著:「三里內庭穴,曲池合谷接,委中配承山……」
事實上,我這一次也沒入心,不時偷瞄著老張頭是不是在看著我——果不其然,他也在盯著我。
日子長了,老張頭就經常來中醫館了。一開始他總是很沉默,來了就縮在角落里,扎完針給了錢就走,話也不多說一句。但是我相信,老年人的沉默都是長期孤寂生活的習慣性行為,他們渴望理解和交流,年歲越大,能與之一同交流的人就越少。每次在病床上躺著的老張頭,聽著其他老年病患侃侃而談,時不時也會吸一口氣,嘴角抽動一下,做出要開腔的準備。
來中醫館的老人更多一些,有的老人甚至一天來好幾趟。可能也不為治病,就是踏進中醫館的門,看見了醫生,這病就舒緩一半了。
大部分的老年病患都是這樣的,他們身上的病跟了他們三十年、四十年、甚至更長,早變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。一生的支離破碎和病痛代表著死神,那個一出生就在追趕他們的死神,在生命最后的幾年,他們慢慢感覺到死神就要追上自己了,也就不苛求什麼藥到病除了,醫生給他們更多的只是某種希望,多于祛除病痛。
在老張頭來中醫館的一個整月后的那天,可能他也覺得自己在這片地方熟絡了,可以慢慢說話了,第一次和其他「兄弟姐妹」攀談了起來——人家聊天,他插話進去,大家都是老年人,這種行為并不討厭。只是老張頭討厭,他說話總是很偏激,能把一個好好的話題扯得「非親非故」。
「看新聞了嗎,香港那幫人,看吧,鬧不了多久了,就欠收拾,一收拾全玩完!」長了蛇盤瘡的李大爺如是說道。
「那是,你看看這麼多年台灣新疆西藏,天天鬧來鬧去的,誰獨立了?」因受風面癱的劉大爺,硬著嘴唇也隨聲附和。
老年人聊天都這樣,什麼觀點,大家都捧著聊,不細追究誰對誰錯,越聊越熱鬧。
可老張頭不,他帶著孩子式的逆反心理,非但不捧任何人,他還拆台,不贊同任何人的觀點,哪怕人家是對的,他也得說錯,并且自有一套歪理。
這次就是,劉大爺剛附和完,老張頭緊接著「哼!」了一聲:「那個小破地方,不要就不要了!電影沒看過嗎,多亂啊,天天砍人!」
三個老頭就台海問題和香港問題,開始深入交換意見。老張頭嗓門最大,因為他最沒理。話題越來越偏,我很想象裕泰茶館的王利發一樣,在柱子上貼一張紙條。
給老張頭拔了針,他看了看仍意猶未盡的劉大爺和李大爺,撇下一句「你們倆還是什麼都不懂」,穿了衣服,瀟灑離開了。
自此以后,在中醫館里,張奶奶買雞蛋買貴了,老張頭要說買便宜了;李阿姨說早市的菜好,他非說超市的更好。什麼事在他嘴里都和別人不一樣,無理也要辯三分。慢慢地,聊天的老人變少了,尤其老張頭在的時候,幾乎都沒有人說話,老了老了,倒修煉成了杠精。
但是也有老張頭插不進嘴的話題,那就是兒女問題。老人們在一起除了聊雞毛蒜皮,就是說各自的孩子,甚至是孩子的孩子。但是大家從沒見過老張頭的孩子,甚至關于這個話題,老張頭提都不提。
李大爺痊愈的第二天,又來了中醫館,一是付清藥費,二是找人聊天。他一屁股坐在了老張頭的衣服上,然后站起身,邊為老張頭疊衣服,邊仰臉笑:「老張我跟你說,這次咱倆得接著嘮嘮上次沒嘮完的事兒。」
老張頭也不示弱:「嘮唄,時間還不是有的是嘛。
」
然后,兩個老頭就結合著最近的「中俄海上軍演」開始了討論。
李大爺揚揚手:「你說這老毛子是厲害啊,我看網上那個貝雷帽的照片,真算得上精悍啊!那才叫兵!那才是打仗!」
老張頭必然反駁:「貝雷帽有咱解放軍特種兵厲害麼?比咱厲害還用得著跟咱聯合?」
「那不是給美國人看的嘛?」李大爺追了一句。
老張頭搖了搖身體:「都說了‘不針對第三方’,就是普通的軍演,什麼年代了你還看新聞——現在什麼消息都是上網看,跟不上時代咯你這老趕!」
李大爺氣得咬牙,長嘆一口氣,抱著膀回擊:「我兒子跟我說的,他參加這次軍演了,我兒子不能騙我。」
老張頭不犟了:「那你兒子說的對!」說罷,他就起身要走。
這一下把李大爺給閃個趔趄——說好的往下杠,怎麼突然不杠了?可能李大爺早就想好了要是老張頭杠他兒子怎麼辦,早在心里打好腹稿回擊了,可這一句「你兒子說的對」,讓李大爺把都到嘴邊的話給憋了下去,而且噎得夠嗆,贏了辯論也不開心了,索然無味。
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,老張頭在中醫館不再什麼話都接、什麼岔都打,更多的是靜靜聽別人說,也可能沒聽,但是一直是靜靜的。大家也漸漸明白了,很有可能,老張頭是沒有子嗣。
大家也就不提了。
轉過了年,老張頭就不常來了,中醫館的老年病人也已經換了一大批,有些人離開了,有些人回來了,有些人再也回不來了。有的時候忙忘了很多事,突然想起來某個老人怎麼這麼長時間不來了?才幡然醒悟,可能是過世了——也可能是一直沒再生什麼病,總之,不敢細想。
老張頭和老伴兒再一次來中醫館的時候,帶了一個孩子和一個女人。孩子坐在老張頭的腿上,疑惑地看著身邊的人,那個女人拎著老張頭的坐墊和一個包,和老張頭毫無交流。
我第一次看見老張頭笑,他笑著對我父親說:「這是我外孫子,不是咱東北的小孩,有點水土不服,你給捏咕捏咕。」
孩子看起來也就四五歲,特別白凈,白里透紅,眼睫毛極長,臉蛋也潤,上面沒有東北孩子特有的紅血絲。
孩子一從姥爺的腿上離開就哭,老張頭兩個大手抱著孩子的腰:「不哭不哭,不疼,咱不扎針,就捏捏揉揉。」
孩子是深圳來的,尚且短暫的小生命沒見過如此低溫的嚴寒,沒見過摞成小山的排骨,沒見過溜肉段,也沒見過鍋包肉和酸菜燴血腸——孩子腸胃不好,估計是突然大魚大肉給喂的,又因為太冷了,得了重感冒。
但重要的是,朗朗蒼穹下,老張頭沒有子嗣的「謠言」不攻自破。
之后老張頭每一天都帶著孩子來,那個女人有時來有時不來。因為有了孩子,滿是蒼老生命的屋子里添了很多生氣。
老年人總愛問那麼幾個問題:「爺爺好還是姥爺好?」「奶奶好還是姥姥好?」對于這個孩子,還可以再多一個,「深圳好還是東北好?」
這些問題幾乎每天都有人問,老張頭總是笑瞇瞇地看著小外孫回答「姥爺好」「奶奶好」「深圳好」。老張頭根本不在乎別的,只一句「姥爺好」就澆了他一心頭的蜜,至于其他兩個回答,「那說明我們家孩子誠實不撒謊」。
小孩子從冬天蹦跶到了開春,熟悉了鍋包肉,熟悉了堆成山的排骨,熟悉了酸菜燴血腸,也就要走了。可能是小學,也可能是幼兒園,要開學了。
很明顯,能看得出來那幾天老張頭又回到了從前那樣,眼神也變得木木的。他最后一次帶孩子來中醫館,開一點中藥治孩子的胃病。孩子媽媽拎著行李箱,開完藥,就準備直接去火車站了。
在無人說話的寂靜時刻,老張頭又蹦出了好幾句有的沒的。
「孩子可得按時吃藥啊!」
孩子媽媽點點頭。
「給孩子多吃肉,別老清湯寡水的,長身體呢,看看孩子瘦的。」
孩子媽媽照舊點頭。
「夏天孩子放假了,給我帶回來,我想外孫子!」
孩子媽媽,一改沉寂,把孩子從老張頭腿邊扯回自己手里:「根本就沒有胃病,他不能吃太油膩的你們也一直喂!回不回來不一定呢,反正現在微信也方便,能看見就行唄!」
老張頭站起身就要抬手打人,但是他可能又覺得外孫子在這兒不太體面,轉而直指孩子媽媽的額頭:「你不回來都行!孩子必須給我送回來!」
「給你?再說吧!」孩子媽媽一把抓住孩子,奪門而去,藥也沒拿。老張頭看著他們離開,知道自己追不動的,只能把藥掖進了懷里,又使勁按了按。
他對我擺了擺手,也走了出去,很明顯能感覺到,再次起身的時候,他的身體好像被人拿走了什麼,步履都特別無力。
外孫子走后的第二天,第三天,老張頭連著打來電話,讓我父親過去看看他。他在電話里聲音很虛弱。
我和父親去了老張頭的家,兩個臥室中間隔著一個客廳,左側住著老張頭,右側住著他的老伴兒。昏暗的小屋里,有被撣單蓋著的電視和電風扇,白色的傢俱都泛黃了。我還看到一個癟了的足球和一雙很舊的球鞋。
孩子走的第二天早上,老張頭就起不來床了。強行起身站了起來,走了幾步就摔倒了。這種年齡的老人摔倒是很危險的,但是幸好,他還想得起來打電話。而老伴兒也是在那天和老張頭「分居」的,美其名曰自己睡覺打呼嚕,怕吵著老張頭睡覺。
我看見了擺在電視旁邊的照片,除了老夫妻倆和女兒,還有一個男人。
男人眉宇間的狀態和老張頭簡直一模一樣,但是我沒見過這個人。
我問老張頭,這男的是誰。
老張頭精神頭回來一點:「我兒子!」
「那怎麼平常看不見他啊,工作忙啊?」
老張頭微微一笑:「國外呢,踢球呢,這小子從小就踢球踢得好,現在踢去國外了。」
具體是什麼國家,老張頭說不清楚,老張頭只知道是給學校里的學生做陪練,掙不了很多錢,但是兒子開心,就支持。
老張頭給了我一張他兒子的單人照片,照片后面寫著「我在伯納烏」。老張頭恐怕不知道伯納烏是什麼地方,但是看得出來,兒子是他的驕傲。只是這份驕傲,讓他說不清國家,也不知道具體掙多少錢,更何況,可能兒子總也不回來。
「你怎麼不叫你老伴兒給我打電話啊!」我與他閑聊。
「她聽不見了!我說啥她都聽不見,我昨天摔地上了她都沒聽見!耳朵不行了!」說完,老張頭一臉惋惜,又在喃喃自語了,「許也是想孫子想得上火吧。
」
絕對不是——我心想,剛剛進屋,我們跟他老伴兒也有交流,都很正常,至少不會那麼聾,或者老伴兒跟他是裝出來的,純粹不想和他有任何交流——可千萬別是這樣啊,我心想。
在老張頭不來中醫館的日子里,大家也沒覺得少了什麼。日子就是慢慢在不知不覺中把每一個人都泯滅掉。
父親兩天去給老張頭扎一次針,有的時候也會忘,忘了就會收到老張頭打來的電話。
「我估計得給老張頭扎到走。」父親在一次回家以后跟我這樣說,語氣伴隨著無奈。
在這一年夏天,小外孫子沒有回來,老張頭徹底不能動了,甚至開始糊涂。對于老伴兒的耳聾,老張頭深信不疑。在他臥床不起的日子里,老伴兒負責他一日三餐和兩次排便。一天見五面,兩人都無話。
老張頭的家變得又酸又臭,我和父親再去的時候,門簾比原來更油膩了。老張頭躺在床上望天,老伴兒在自己的屋子里看電視,有的時候老張頭忍不住要喊兩嗓子,電視的聲音就會被調大,他不喊了,聲音也小了。我們和他老伴兒正常交流不必刻意大聲,但是老張頭在隔壁屋怎麼喊,就是不會被聽見。
老太太對我們說,他們兒女雙全,但是老張頭重男輕女,因為老大是女兒,所以必須要一個兒子,不然就斷了他們家香火了:「我們家閨女打小就懂事,也學習好,白凈、個高,人見人愛的。他非得讓孩子念到國中就不念了,我好說歹說讓孩子讀完了高中,他非要讓孩子上班。」
說到這兒,老張頭又在那邊屋子里喊了:「能不能看看我啊!我拉了,肚子疼!看看我啊!聾子!」
「我不恨他,過一輩子了,我得管他,但是現在我真是看見他我就夠了,我恨不能開了煤氣罐都死了得了!」老太太屁股都沒挪一下。
我往隔壁指了指:「那他在床上……不用處理麼?」
老太太對我擺了擺手:「我會給他拾掇的,他躺了這麼長時間沒有褥瘡,我不會不管他。」
中醫館里唯一一個曾經認識老張頭的人,在後來告訴我,是老張頭過于重男輕女,強行把女兒送進深圳的工廠上班的,他過于溺愛的兒子不學無術,偷了家里所有的錢就去了北京,在北京待了幾年就跑去了國外,再沒回來過了,跟家里也很少聯系。春節時女兒帶回小外孫子,是緩和之意,但是老張頭只看見了小外孫卻沒看見女兒的真心實意,攜手一生的妻子也因為老張頭這樣的剛愎自用而裝聾作啞。
老張頭的晚年不可謂不可悲,可是沒得怨。
到了2020年,老張頭至少10年沒見過兒子了,4年沒見過外孫了,也4年沒見過女兒了——當然,他可能不在乎這個。我父親的年齡也大了,事情也多了,給老張頭扎針的事情就落在我身上,如今也有2年了。
年初疫情爆發,大年初二封城以前,我給老張頭家送去了10個N95,但是他們老兩口對于疫情毫無感知,疫情對他們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沒有了針灸的寬慰,老張頭能不能熬得過這段日子。封小區后,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沒再去老張頭家給他扎針,撥去電話,所幸一切都還好——老張頭仍然和當年一樣難以入睡,但身體和當年差很多了。在這段日子里,老張頭最渴望見到的是出走多年的兒子,和4年不見的外孫子。
其他的,都不想。
解禁以后,我急急忙忙地去了老張頭家。屋子里毫無生氣,所有傢俱上都落了一層灰。老兩口吃了半個月面條了,不是買不到新鮮蔬菜,而是害怕外面不安全不敢出去。
老張頭向我表達了對兒子的思念,但是太長時間沒聯系兒子了,手機也摔壞了,屏幕看不太清晰了。
「用微信聯系啊。」我對老張頭說。
「一直沒有加過微信,都是等他來電話,我們也打不回去。」老張頭含著淚對我說。
也是巧了,就在扎針的時候,手機響了,竟然是遠在國外、根本不知道在哪個國家的兒子,也許是西班牙吧,我猜想。
「老兒啊,真是你啊?誒呀疫情怎麼樣啊你們那?」老張頭的哭泣讓門外本應該「耳聾」的老太太聽見了,老太太過來,奪過手機帶著哭腔:「能不能回來啊,現在外面不安全啊!」
我根本聽不清電話里說的什麼,大概意思就是無法回國,票價很貴,而且沒錢。老張頭一時找不到話,就把我給他扎針的事情敘述了一遍。老年人就是這樣,說話抓不住重點。
在我的提示下,老張頭的兒子留下了微信號,這麼多年居然才加上微信,我也是很驚訝。為了給兒子省錢,老張頭讓兒子保重身體,就匆匆掛斷了。掛了電話以后,老張頭心神好了很多,我以為他兒子會緊接著就撥來視頻,但是沒有。我走之前,很想撥過去一個視頻,但是老張頭不許。
「不打了不打了,聽見說話很好了,萬一忙呢,有時差,估計睡覺了。」老張頭抱著手機躺在床上,眼角含了一塊眼屎對我說。
送我離開時候,老張頭的老伴兒一臉沉寂,她還沒跟兒子聊幾句話,她也想兒子,女兒已經被老張頭變相趕走了,好不容易盼來兒子的電話,卻不能說幾句話,老張頭真的太自私了。
「小孫吶,以後來你就直接進屋吧,不用敲門了,平時沒人來,來了就是你,我以后也不鎖門了,現在歲數大了,起身開一次門可費勁了。」老太太邊走向自己的屋子邊說著。
後來沒有多久,舒蘭的疫情就又開始了,我和老張頭又斷了聯系。等再去老張頭的家里,他已經把在電視柜上的全家福擺在了自己的床頭,肯定是老伴兒幫忙拿進屋的。老張頭常常拿著照片對我說:
「其實我兒子可聽話了,閨女也懂事伶俐,小時候我去接他倆放學,個個爭著騎我自行車,騎座上根本夠不到腳踏子,誒呀。」
「我那個時候是單位‘五七工’,有的時候拿點單位的廢料鋼鐵,給他倆打的筆盒,結實。大閨女有一個發夾還是我打的,但是人家嫌不好看,沒戴過。」
「有一次我兒子喜歡電視上跳踢踏舞的,非讓我在布鞋上縫鐵片,我罵他是野驢不用釘蹄子,人家最后到底在鞋底下扎了兩個鐵扣子,主意正!隨我!」
我相信沒有人愿意和老張頭聊天了,也不會有人和他聊,他的這些回憶如跑馬燈在腦海浮現,一幕又一幕,都是他過完的一生。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風雪貫徹的夜晚,我每天來到老張頭的家,帶著銀針,為他的火盆攏一捧火,可老張頭總是踢翻自己的火盆——一個人到了晚年時,任何的火都無濟于事,我和他都清楚,每次給他扎針已經不能緩解他什麼了,他一生的寒冷太巨大了,而針的力量杯水車薪。
(編者注:「五七工」是指20世紀六七十年代,曾在石油、煤炭、化工、農、林、水、牧、電、軍工等19個行業的國有企業中從事生產自救或企業輔助性崗位工作的、具有城鎮常住戶口、未參加過基本養老保險統籌的人員。這些人員多數在當時初響應毛澤東「五七」指示,走出家門參加生產勞動,進入企業不同崗位的城鎮職工家屬,因此統稱為「五七工」。
)
終于在這個暴雨的季節,他沒熬過去,也可以說,他是被暴雨帶走了。
老張頭臨走前,曾突然給我打來電話,質問我為什麼不來給他扎針。我對他解釋,昨天剛扎過,隔一天一次,你怎麼忘了?老張頭不管,在電話那頭大喊大叫,叫我去給他扎針,「不扎針睡不著覺!」
我開著車在暴雨里疾馳,我不敢停車,怕他等急了,也怕車熄火以后就沒辦法發動了。街面上一個人都沒有,這麼大的雨誰上街誰是腦袋大!但是為了老張頭,我不得不如此。我邊開車還邊盤算著——今天扎什麼針,馬丹陽十二穴我還是沒學會,只能是用內關神門三陰交,再按摩按摩百會了。許是雨下得太大,他興奮吧。
我到了,老張頭目光炯炯,說自己睡不著覺,我并未扎針,只是給他揉了揉,說了幾句寬慰的話,就要離開,我不想因為太大的雨回不了家,我也沒注意到老張頭反常亢奮的神態。
走出屋外,老張頭還在大喊大叫,可是喊的什麼我都沒聽清。老張頭的老伴兒依舊送我離開,指著老張頭的屋子一臉抱歉地說:「以后可別活這麼大歲數,麻煩人,不招人待見了。」
「雖然都說活這麼大歲數不好,但也沒看誰真那麼想死,您說是不是。」我憨憨地回答。
我倆互相笑了幾下,我便離開了。坐進車里,我突然想起來一個中醫名詞,「假神」,即「久病之人精神轉佳,言語不休,兩顴泛紅如妝,精氣衰竭至極陰不斂陽」的好轉假象。
我一個激靈,立馬把車開回,上樓而入,果然,老張頭走了。
老太太也從旁屋進來了。
「我……這……」我一時啞口不知道說什麼好。我下意識地想跟她說清楚我跟老張頭的死沒關系。
老太太看出來我的意思,對我擺了擺手:「死了?」
我木訥地點了點頭:「差不多吧,剛才那麼亢奮,是回光返照。」
「跟你沒關系,死了好,不受罪了,我也輕省了。」她慢慢走到床邊,握起來老張頭的手。
「用不用我幫你打電話,或者有沒有什麼其他親戚啊?」我有點害怕地問。
「不用了,都不用了,我們也沒啥親戚,你走吧小孫大夫,你走吧!」說罷,老太太就起身推我,一直把我推到門口,略帶哭腔地對我鞠躬感謝我,「這幾年辛苦你和你爸了,以后不用了,都不用了。」
她把我推出門,那個說好了不為我關的門重重地關上了,門的力道讓我確信有一個老人在背面倚著。我還沒走出一步,就聽見了里面的哭聲,先是很低,越來越高,越來越不能止息地哭。
那是痛苦麼?還是解脫?
無論如何,我撥打了120,我知道沒什麼用了,但是老張頭總要從樓上下來。
我們都是自己的殉道者和守墓人。老張頭死了,就像雷雨里的周樸園,堅持著自己的封建觀念,最后在一場大雨里送了他的家人,成為了他封建信仰的殉道者。老張頭死了,我們在雨中相遇也在雨中分離。老張頭死了,沒有外傷沒有褥瘡,最后幾年除了枯燥乏味卻也體面地死了。老張頭死了,磅礴的雨聲蓋過他本應該響徹天際的哀樂。老張頭死了,無人發送。
注:為了篇幅考慮,本文有一定刪減,原文查看可至:一個老人,和他封建信仰的死亡
作者:孫思遠
編輯:許智博
本文系人間工作室獨家約稿,并享有獨家版權。如需轉載請私信。
投稿給「人間」非虛構寫作平台,可致信:[email protected],稿件一經刊用,將根據文章品質,提供單篇不少于3000元的稿酬。
其它合作、建議、故事線索,歡迎于微信后台(或郵件)聯系我們。
更多信息,移步微信公眾號:人間theLivings(ID:thelivings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