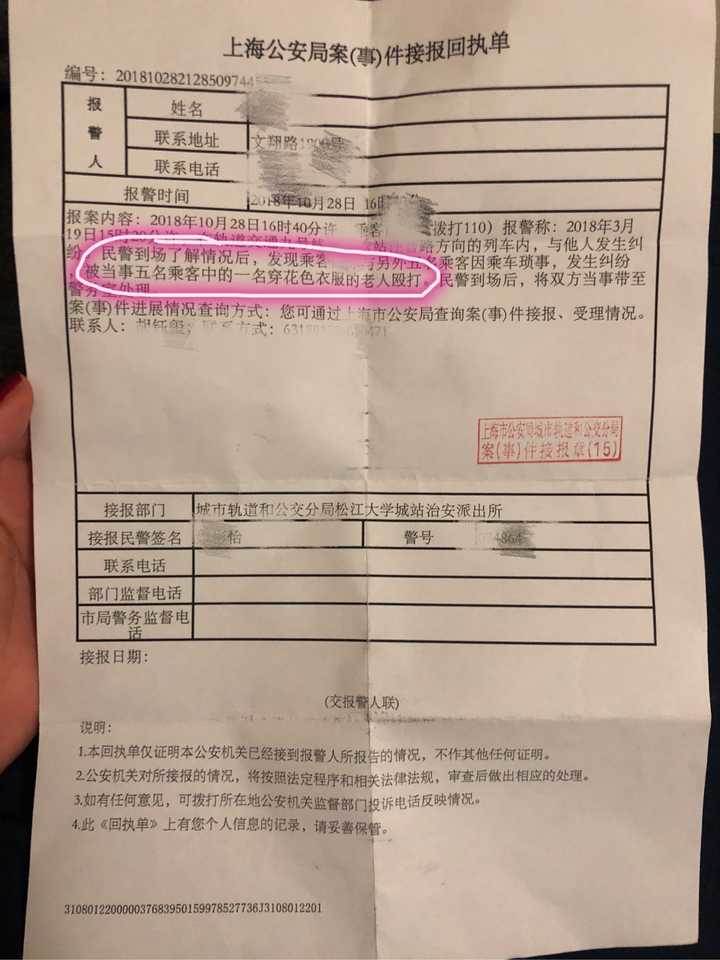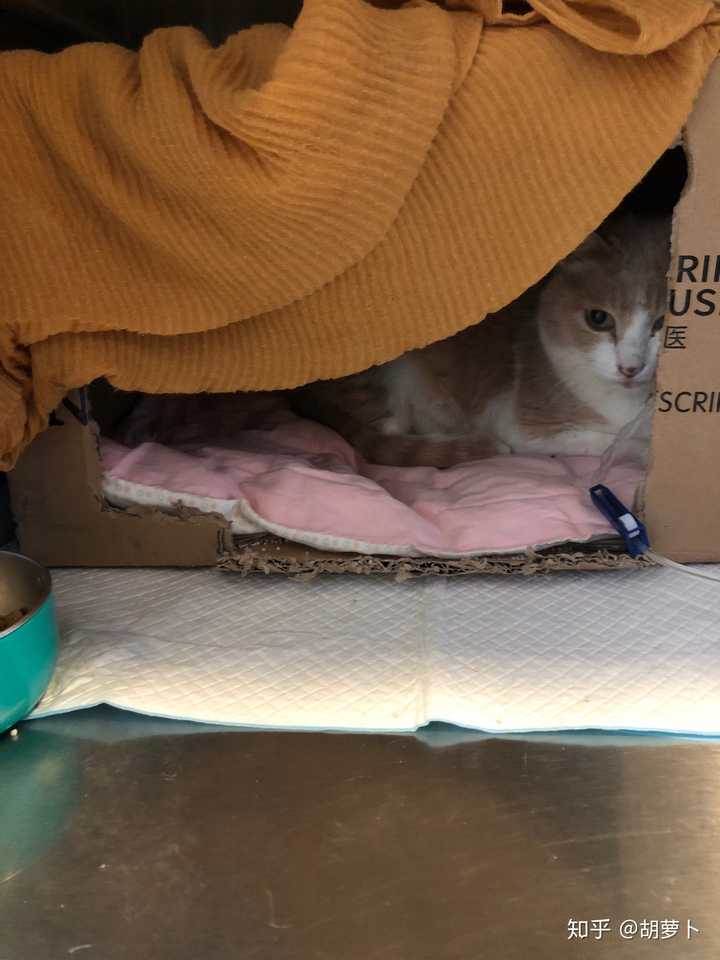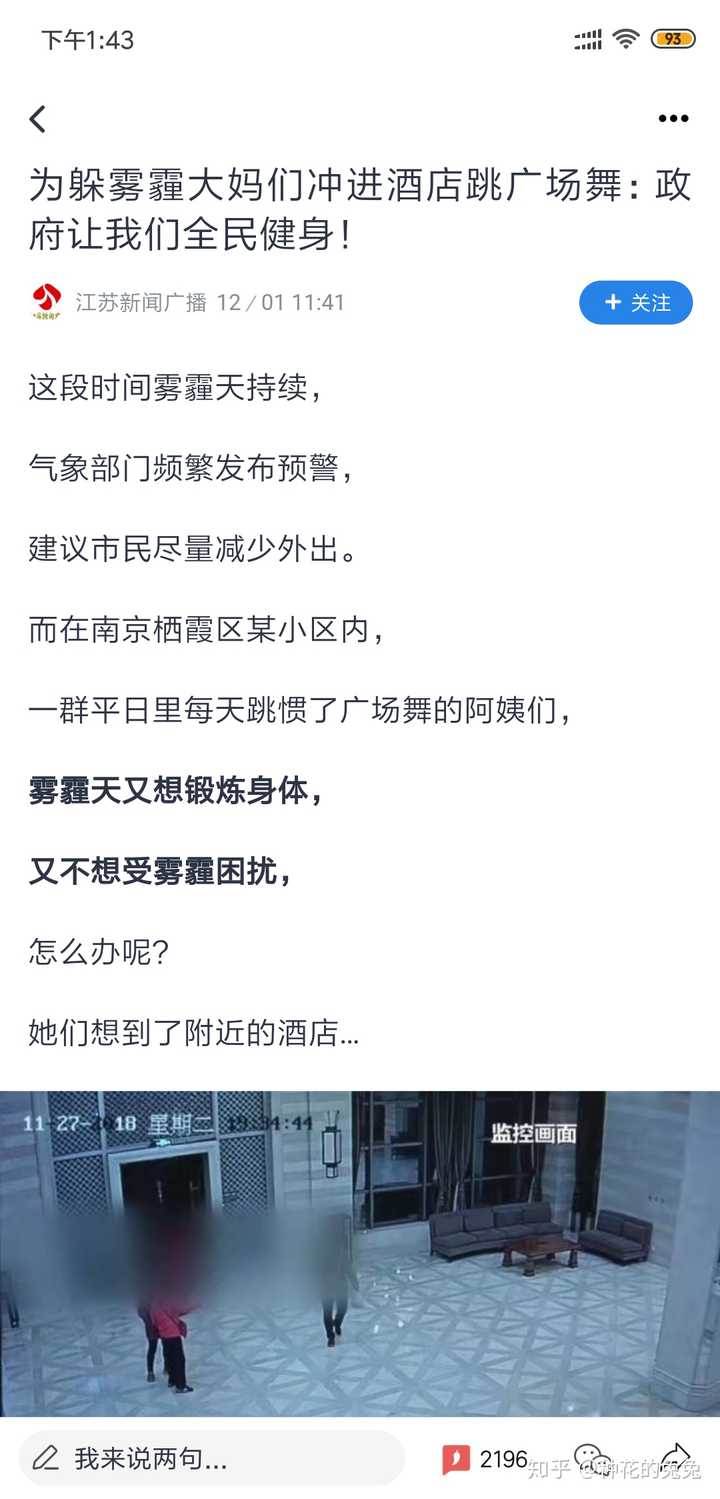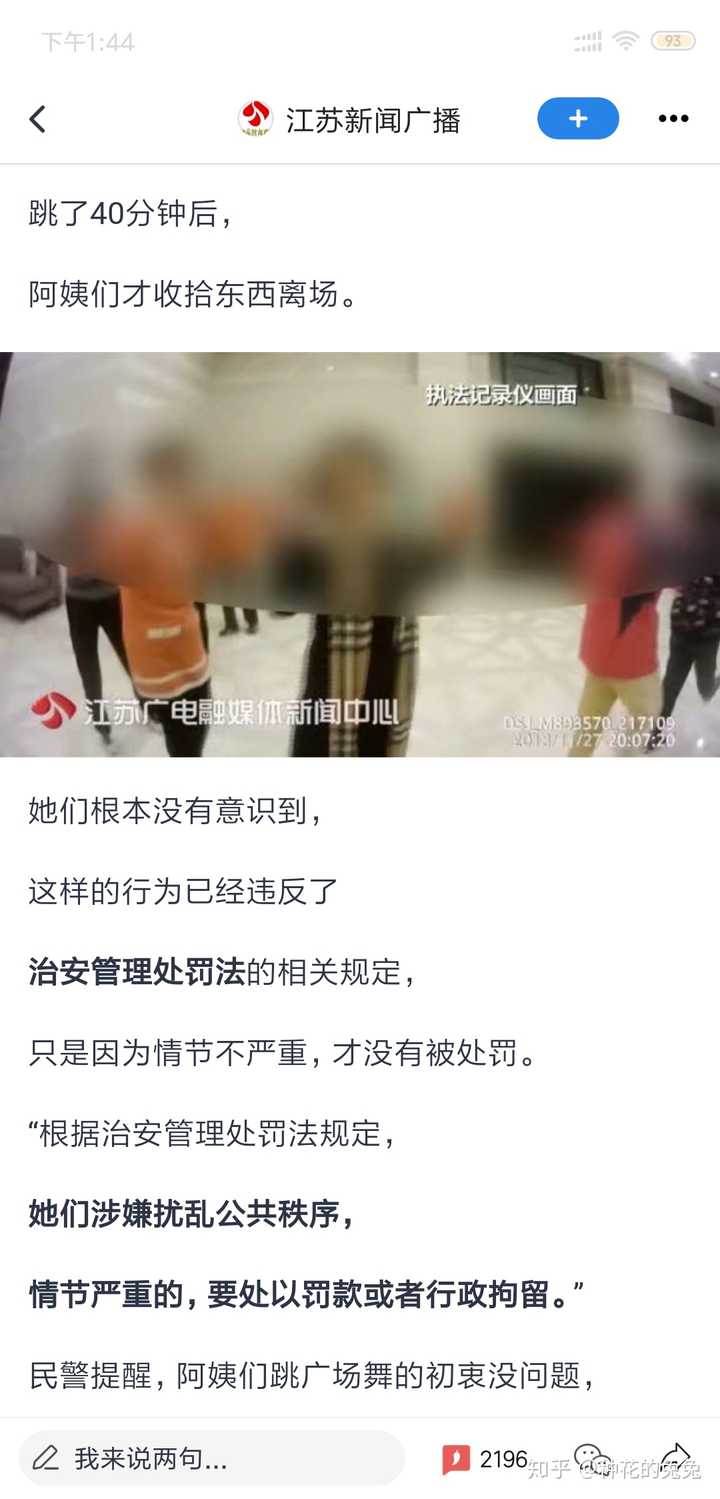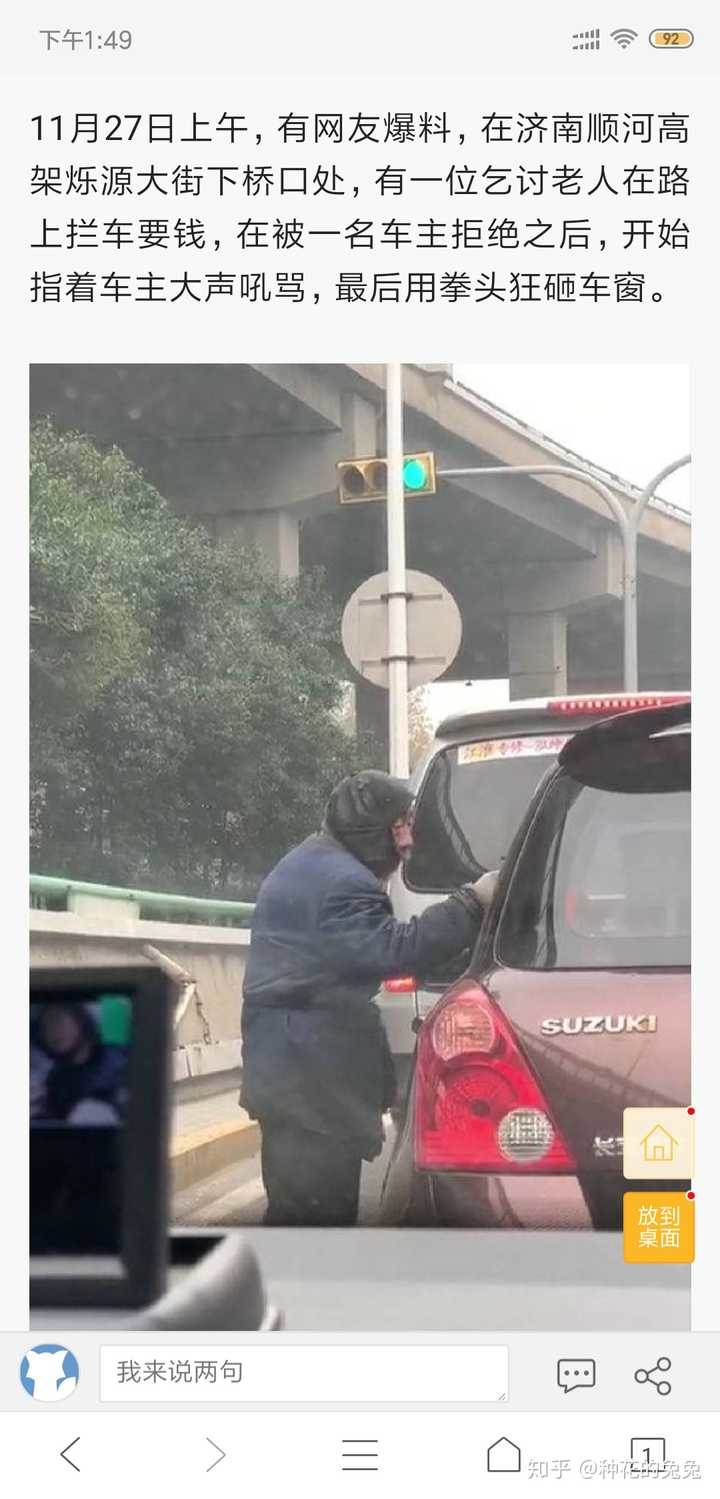少年,我給你講個故事吧。
奶奶年輕的時候是東西兩村里最出名的「老婆天兒」,輩分兒大,脾氣更大,動不動就叉著腰站在街頭上破口大罵,一般人都不敢招惹她。
聽我爸說,鄰村的一頭牛因為在奶奶家門口的路上拉了一泡屎,就被奶奶抄起一塊磚頭砸瞎了眼睛。
奶奶還年輕的時候,也就是爸爸小的時候,家里兄弟姐妹多,橫七豎八的睡滿了一大炕。人多以后,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吃飯的問題。奶奶作為這個大家庭的總管,自然要省吃儉用,平日里炒菜放到鍋里的肉最后都要用筷子再一塊一塊挑出來,日子過得比誰家都緊巴。
這兄弟姐妹里,叔叔最淘。有一次,他把奶奶要留著過年的一斤肉偷炒著吃了,被奶奶在三九天的鵝毛大雪里用掃帚趕出了家門,穿著秋衣秋褲在柴火垛里餓了一整天,差點凍死。
爸爸小時候最老實,基本上不干出格的事,但是也有一件有意思的事。那時候白糖特別貴,家家戶戶都缺白糖。有一回,奶奶讓爸爸扛著一大袋子「白糖」送到鄰村老孫叔家,爸爸扛著「白糖」一路子上都惱火,兄弟姐妹們幾個月都吃不到一點白糖,這一下就給人家送了一大袋。半路上他越想越氣,用手把袋子上摳了個窟窿,狠狠地抓了一把,一口填進了嘴里。結果被粗鹽齁了個半死。
奶奶重男輕女的思想特別嚴重,不僅表現在對自己的兒子和女兒差別對待,對生兒子和生女兒的兒媳婦也是區別對待。
這一點特別招人恨,媽媽對我說,家里還沒有我的時候,奶奶就經常沖著媽媽亂發脾氣。
因為大娘嫁給大爺以后馬上就懷了哥哥,而在跟爸爸結婚以后的第一年里,媽媽沒懷上。
奶奶抱上第二個孫子的愿望等了一年還沒看見個影兒,特別生氣,變著法兒的挖苦媽媽。
指著母雞說,看著好好的只母雞,咋就不下蛋呢。
媽媽又氣又委屈,還不敢頂嘴,只能偷著哭。
結果到了第二年,媽媽懷上了姐姐,但那時候做B超的少,不知道懷的是男是女,所以一直到姐姐出生前,是奶奶對媽媽最好的時候,破口大罵的時候少了,有時候還往我家里送些雞蛋和小米。
姐姐出生那天,是八八年的陰歷七月十八,天兒熱的人喘不過氣來。
媽媽在這樣的三伏天里經歷了天下第一疼的分娩以后,迫不及待的看看姐姐,姐姐生的腿兒也長皮兒也白的,特別招人稀罕,媽媽心里也高興,可是一想到生的是女孩,想到奶奶不知道會說什麼,媽媽心里又蒙上了一層灰。
聽媽媽說,奶奶聽到生的是女兒的信兒的時候,一句話也沒說,像聾了一樣。
從姐姐出生到我出生之間的這四年里,媽媽像活在地獄一樣。
媽媽坐月子只坐了不到30天,地里的花生熟了,媽媽就在奶奶的嘮叨聲中下地干活兒去了。
農活兒的辛勞,八月的酷暑,讓媽媽落下了一身的月子病,直到現在,媽媽才五十歲,就已經渾身都是病。
最讓媽媽難過的是,奶奶因為重男輕女的思想,根本不愿意幫媽媽照顧姐姐。那時候媽媽白天下地干活,傍晚回來就要馬上去奶奶家把姐姐抱回家,奶奶每次都是牢騷滿腹,難聽的話不斷。回家以后,媽媽為了做飯,就想讓爸爸抱著姐姐,可爸爸一接手姐姐就哭,所以媽媽大多數時候是一只胳膊抱著姐姐,一只胳膊炒著菜。直到現在,媽媽的肩膀還會經常疼,治不好了。
媽媽說,懷我的時候,她就想,如果再是個女的,她就沒法活了。
所以當我帶著那個又小又寶貴的「把兒」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,媽媽就像撿到了救命稻草,把我當成金子一樣的東西,遂為我取乳名:發光。
從我出生后,媽媽立馬就覺得揚眉吐氣的。不過我小時候長得特別像女孩,媽媽恨不得讓我天天當街撒尿,讓十里八村的人都看看她這是個兒子。
奶奶家的那兩顆柿子樹不知道種了多少年了,結出的柿子分給這一大家子都吃不完。我出生之前,媽媽一次也沒吃到過,從我出生以后才有我家的份。那柿子又大又甜,我每年都盼著奶奶提著那一袋柿子來我家送。
可是人生總是十有八九不如意,有時候連那一二也不如意。後來不知道是奶奶稀罕夠了孫子,還是因為奶奶進入了更年期,或者根本就是對一個人的態度成了一種習慣,奶奶對媽媽又恢復了原樣。
我的出生根本沒有對媽媽的生活造成翻天覆地的改變,倒是奶奶對大娘和嬸子那邊的態度也變得跟對媽媽一樣差了。
媽媽印象最深的是去結紮的時候,爸爸騎著那輛當時非常高配的野馬100摩托車載著媽媽回到家的時候,已經八點了。摩托車還沒進院,奶奶的辱罵聲就傳了出來,發動機的噪音也蓋不住她嗓音的高亢。從門口一直到把我抱出門,一句不帶重樣的,一句比一句難聽,罵到「你們還回來干什麼,還不如在路上嘎巴死了呢!」這句的時候,媽媽實在聽不下去了,剛要還口,奶奶抄起一個煙灰缸啪的一聲就摔在水泥地上,玻璃煙灰缸摔得粉碎。
媽媽嚇得不敢大喘氣,一聲不吭、毫無表情的把我抱回了家,奶奶跟著罵了一路,一直把媽媽「送」到家。
嬸嬸脾氣倔,受不了奶奶也對她罵罵咧咧的,不知道哪次把她罵了開始,嬸嬸有五年時間里沒到過奶奶家一次。
不僅平時不去,過年過節也不去,出門都避開奶奶家門口那條路走。
大娘和媽媽雖然去,但也只是像固定的流程一樣走個過場,不多說一句話,也不少說一句話。
奶奶家橫七豎八睡滿的那一炕人,慢慢的長大,慢慢的分開,疏遠去了。好像從那兩棵樹上生出的柿子,後來柿子都聚在一起,卻沒有人再去討論是從哪顆樹上摘來的了。
我念高中的時候,因為住學校里,便很少再到奶奶家。高二那年,爺爺左腳得了骨質增生,而且越來越嚴重,拄著拐杖都要挪著走,生活起居全靠奶奶一個人照顧。最可憐的是,因為左腳神經的壓迫,爺爺開始大小便失禁,哪怕穿了尿不濕,每天早上起床,褥子上還是臭烘烘的一片。
奶奶每天都給他洗衣服和褥子,給他做飯吃。雖然嘴上罵罵咧咧的,但手里的活兒從來沒停下過。
後來工作以后,我離家很遠,每年只回去兩次,我每一次都發現奶奶佝僂的身子因為衰老而逐漸蜷曲,萎縮,本身就單薄的身材因為日夜的操勞,瘦骨如柴,干癟的皮膚充滿了褶皺,緊緊的貼在細小的骨架上,不可反抗的暗淡下去。
我每次都爺爺斜著倚在那張破爛的沙發里,左腳用一塊棉布擔起來不觸地,嘴角不可控制的流著口水。
奶奶每次從我進屋就開始嘮叨著要給我拿些柿子,東屋西屋的找袋子,再把那些柿子一個個擦干凈放進去,那些柿子一如既往地又大又甜,我卻再也吃不下。
每次我走之前,她都要蹣跚著身子再追上我,讓我等著,再快走兩步,從小南屋里拿出一袋小米或者一箱牛奶,急切又小心的說,這是誰家拿來的,肯定很好,我們吃不著,你快拿回家給你媽吃吧。
我幾次從奶奶家出門的時候,都是轉過頭眼淚就滴到了地上。
我不知道這些夾雜著太多瑣事的親情該怎麼去描述和定義。我也逐漸明白,這世界上沒有完全好的人,也沒有完全壞的人,絕大多數人都不可避免的在歷史的長河之中隨波逐流,唯一不變的是時代的變遷、觀念的轉變,歲月的流逝和生命的垂危。